The Walls around Us
| 作者 | Nova Ren Suma |
|---|---|
| 出版社 | 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 |
| 商品描述 | 圍牆:《紐約時報》年度暢銷作品,入選愛倫坡獎最佳青少年讀物《學校圖書館期刊》、《波士頓環球報》年度最佳圖書小鎮劇場後方的隧道裡,發生了一起駭人聽聞的殺人事件。芭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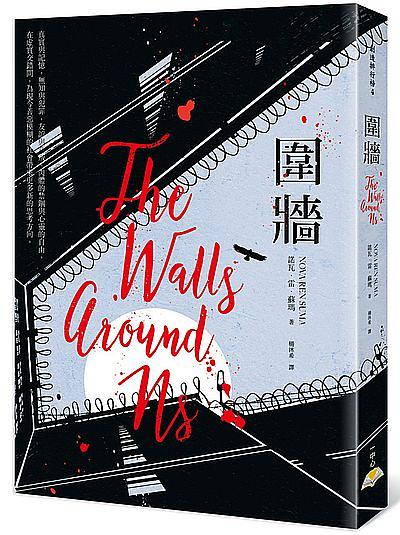
| 作者 | Nova Ren Suma |
|---|---|
| 出版社 | 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 |
| 商品描述 | 圍牆:《紐約時報》年度暢銷作品,入選愛倫坡獎最佳青少年讀物《學校圖書館期刊》、《波士頓環球報》年度最佳圖書小鎮劇場後方的隧道裡,發生了一起駭人聽聞的殺人事件。芭 |
內容簡介 ◎《紐約時報》年度暢銷作品,入選愛倫坡獎最佳青少年讀物 ◎《學校圖書館期刊》、《波士頓環球報》年度最佳圖書小鎮劇場後方的隧道裡,發生了一起駭人聽聞的殺人事件。芭蕾舞界的明日之星鋃鐺入獄,而她的好友取而代之,成為眾人關注的焦點。三年後,看似完滿落幕的事件卻又悄悄浮上檯面,當年事件的真相究竟為何?另一方面,坐落於北方邊境的曙光丘少年懲治中心,以高聳的圍牆與外界阻隔開來。在夏夜一場奇遇後,渴望自由的囚犯們不禁懷疑起腦海中閃現的詭異畫面,是記憶?抑或是幻覺?而這似乎與那位剛入獄的女孩息息相關……諾瓦‧雷‧蘇瑪以優美的字句,譜寫出青少女罪犯們內心最深沉的渴望,以及充滿惆悵的人生境遇。
各界推薦 「懸疑的傑作,絕佳的鬼故事,會毛進你的靈魂裡,久久不散。」--《絕美魔力》作者/黎芭‧布瑞「諾瓦‧雷‧蘇瑪以絕佳的語言、時間線的轉換及不可靠的敘述者們,細致探索才華與平庸、富有及貧窮、勇敢與膽怯之間的權力平衡,以及這座天秤傾斜時,又是如何演變成這般令人不悅的事件。可以說,最後每個人都以《靈異第六感》般的超自然轉折,得到了應有的下場。」--《紐約時報》「《圍牆》是女孩們以各種方式築起高牆、躲藏、建立柵欄的熱情見證。本書文筆絕佳,醜陋的真相加上引人入勝的鬼故事……『我對炸彈的認知就是,炸彈本來就會爆炸。』這是其中一位主角安珀的觀察。爆炸發生時,諾瓦‧雷‧蘇瑪的散文就帶有這種力量及憤怒,而爆炸似乎無可避免。」--《芝加哥論壇報》「諾瓦‧雷‧蘇瑪擅以鮮活的語言創造出超寫實的故事,並聲明『罪行可以輕易頂替,無辜之人應有好下場』這樣的架構,不只能應用在司法系統上,更適用於我們的內心,也就是我們告訴自己的種種說法。這本書帶來一場傑出且驚悚的閱讀體驗。」--《書單雜誌》「……某些人罪大惡極、無可赦免,有些人純真無邪、善良體貼,遊走在兩個光譜之間的人,則也許無害。這種生硬的角色分類並非缺陷,而是作者絕佳寫作功力的展現,即使是憑空描繪恐怖場景,她的想像力都跟一場史詩級舞台演出後的亮粉一樣,揮之不去。」--《波士頓環球報》「青少年過分現實的觀點加上犯罪司法系統體制,為序章展現出些微超自然詭異的氣氛畫龍點睛,之後更升溫成真正讓人寒毛直豎的鬼怪故事。古怪、痛苦、優美,讓人戰慄不已。」--《柯克斯書評》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諾瓦‧雷‧蘇瑪(Nova Ren Suma)哥倫比亞大學藝術創作碩士,曾獲得紐約藝術基金會小說創作補助。小時候曾住在美國哈德遜河谷周邊小鎮,現定居於美國紐約。著有《虛構的女孩》(Imaginary Girls)、《淡出》(Fade Out)、《失蹤者們》(17 & Gone),以及多篇短篇小說。《圍牆》是她的第四部長篇小說,為《紐約時報》排行榜暢銷作品,廣受多方好評。■譯者簡介楊沐希宅居文字工作者,譯有《火星四重奏》、《山姆和我的幸福冒險》、《羽翼女孩的美麗與哀愁》等書。
| 書名 / | 圍牆 |
|---|---|
| 作者 / | Nova Ren Suma |
| 簡介 / | 圍牆:《紐約時報》年度暢銷作品,入選愛倫坡獎最佳青少年讀物《學校圖書館期刊》、《波士頓環球報》年度最佳圖書小鎮劇場後方的隧道裡,發生了一起駭人聽聞的殺人事件。芭 |
| 出版社 / | 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 |
| ISBN13 / | 9789869644501 |
| ISBN10 / | 9869644503 |
| EAN / | 9789869644501 |
| 誠品26碼 / | 2681592724000 |
| 頁數 / | 336 |
| 注音版 / | 否 |
| 裝訂 / | P:平裝 |
| 語言 / | 1:中文 繁體 |
| 尺寸 / | 21X15CM |
| 級別 / | N:無 |
內文 : 安珀/我們瘋了
我們瘋了,在那個炎熱的夜晚。我們嚎嘯,我們肆虐,我們放聲尖叫。我們是一群女孩,有人十四、十五歲,有人十六、十七歲,但當門鎖全部解開、牢房大門敞開,沒有人把我們趕回小隔間時,我們發出了狂怒動物的聲音,男人的聲音。
我們湧進走廊,擠在狹小擁擠的黑暗之中。我們拋下指派給我們的顏色,大部分的人是綠色的,單獨監禁的危險分子是黃色,穿著路邊三角錐橘色衣服的是運氣不好、剛進來的菜鳥。我們脫下連身衣褲,露出自己憤怒、抖動的刺青。
外頭打雷之際,我們占領了A區跟B區,閃電劈下來的時候,我們衝進C區;我們甚至趁機闖進D區,單獨監禁跟有自殺傾向的人都在這裡。
我們就跟等著火柴點燃的汽油一樣。我們齜牙咧嘴,揮舞拳頭,打滑的雙腳在地上咚咚咚地跑來跑去。我們發瘋了,任誰都會。我們傻傻的腦袋又狂又野。你要明白,經過那些讓我們入獄的罪行,經過人家對我們的指控、判我們有罪,我們之中有人毫無悔意,有人發誓自己是無辜的(如果母親健在,我們就用媽媽的名字起誓,
如果養了小狗或瘦巴巴的貓,我們就拿寵物發誓;如果我們誰也沒有,就只能押上自己微不足道的生命)。經過這麼多個待在鐵窗後的日子,今天晚上,我們自由了,自由了,自、由、了。
有人覺得很可怕。
那天晚上,那個現在想起來實在邪惡的八月第一個星期六晚上,位於這個州北邊遠方郊區的曙光丘少年懲治中心裡,只有四十一個人,也就是說,我們還有一個空缺。我們還沒湊足四十二人。
我們很訝異,開心地睜大眼睛,發現B區、C區,還有A區,甚至連D區都是開放的,我們就站在這裡,黑暗裡齊跳的心臟有如雷聲。我們站在牢籠之外,我們站在外面。
我們看著哨亭,裡頭沒有人。
我們看著走道兩端的滑動閘門,都是開的。
我們看著架在高高天花板上的探照燈,燈泡沒有亮。
我們看著(或者說我們想看,因為我們的身體反應就是這樣)窗縫外頭重擊而來的風雨,籠罩整片建築。如果能看透三層圍牆,穿過彎彎曲曲的鐵絲網,繞過警衛塔,抵達陡斜的路,往下走到最底下的高聳鐵柵門,我們就會想起漆成藍色的小巴士從郡立監獄把我們載上來。也就會記得,我們離大馬路沒有那麼遠。
這時我們才會想到,在獄警回到崗位之前,我們可能沒有太多時間。也許我們該提防這突如其來的自由,小心一點。但沒有,我們並沒有停下來質疑打開的門鎖,這個時候沒有。我們並沒有停下腳步思考為什麼緊急警示燈沒有亮,為什麼警鈴沒有大作,也沒有思考為什麼獄卒這天晚上沒有當班,他們可能跑去哪裡?為什麼哨亭裡沒人?為什麼座位空空如也?
我們解散,我們到處跑。我們衝過原本鎖住我們的障礙,我們奔跑起來。
那夜就跟造反一樣爆發開來,混亂霸占了戶外的空地,沒有人曉得其他人在做什麼,根本沒有人在乎。大家又喊又叫,又鳴又嚎。這個州裡最罪大惡極的四十一名未成年受刑人自由了,毫無預警,不用理由,沒有持槍警衛阻止我們。這感覺太美好了,充滿力量,好像手裡握著閃電一樣。
有人根本沒有思考,只想踹爛食堂裡販賣機的玻璃面板,拿裡面的零食吃,或是一掃醫護室裡的藥物,好好嗑個爽。有人想要一拳砸在別人臉上,或跳到某人身上,誰都好,誰都沒差。有兩個人只想溜出去外頭,乘著籠罩的烏雲,在雨中投籃。
然後,還有其他人,有腦子的人,她們喘了口氣,然後動起腦來。因為少了獄卒拿著警棍敲打我們,警鈴沒有響,對講機沒有發出帶著沙沙聲的指令,要求我們回去牢房,那個夜晚的確屬於我們。這是頭一遭,這幾天,這幾個星期,這幾個月,這幾年來的頭一遭。
而一個女孩在多年後首度嘗到自由的滋味,在這種夜晚,她會做什麼?
我們之中最暴力的那些人─親手弒父的人、隨機割喉的人、朝著加油站苦苦哀求的路人近距離開槍的人,她們後來坦承,自己在奢侈的黑暗之中感覺到平靜,這是少年法庭無法提供的公平與正義。
當然,我們之中有人曉得自己不配這種緩刑。我們之中沒有人是全然無辜的。當我們被迫站在燈光下,全身上下,每一個腔室還有填補過的牙齒都暴露出來,我們都不是無辜的。我們面對自己真實的內心時,感覺比目睹法官裁決「有罪」,而整個法庭歡呼起來的那天還要醜陋。
這就是為什麼有幾個人不肯離開牢房,留在原地的原因。我們把圖畫跟情書都擺在自己的小隔間裡,把唯一一把好的梳子跟芮斯花生醬巧克力藏在這裡,因為我們沒有現金,巧克力在曙光丘就跟金幣一樣好用。有人堅守在熟悉的地方。
因為,外頭有什麼?外面有誰能保護我們的安危?
說真的,曙光丘的女孩,不僅讓家人失望透頂,嚇跑英文老師、社工、公設辯護人這些想要伸出援手的人,更危及居住區域,跟垃圾差不多(人家是這麼說的),大家最好都不要想起她(家書是這樣寫的),這樣的女孩還能何去何從?
我們之中有很多人想要逃跑,不過這是習慣使然。有人已經逃了一輩子。逃跑是因為我們還逃得了,更是因為不能不逃。我們為了自己的生命而逃,我們還以為這條命值得。
我們大多跑不了多遠,我們會分心,太過興奮,以為自己戰勝了一切。有兩個人停在人家指派給我們的區域外頭的走廊,滿懷感激地跪在龜裂的地上,彷彿獲判無罪,彷彿過往紀錄都一筆勾銷。
這就好像是我們膽敢讓自己的美夢成真一樣,這是溜進鐵窗間奚落我們的幻想。期待有臺加速逃逸的快車,或能攀著公主的長髮辮,從窄小的窗縫爬出去。我們懇求原諒,懇求復仇,懇求在某個遙遠的世外桃源,能夠展開閃耀的新生,而我們再也不用面對憎恨、法律及傷痛。此刻,我們真的體驗到了自由。我們不敢相信我們這樣的孩子也能遇上這種好事。
有人哭了。
於是,我們在這毫不設防的夜晚重獲自由,立刻想要滿足所有的想像:去最近的公路搭便車遠離這裡;打電話給前男友,好好親熱一下;跑去橄欖園義大利餐廳,吃麵包棒吃到飽;在又大又軟的床上,蓋著蓬鬆的被子好好睡一覺。
那個八月是我在曙光丘的第三個夏天,我將近十四歲時就關了進來(罪名是謀殺,我堅持無罪。開庭時,我把自己塞進裙子跟絲襪裡,法官判決有罪後,我媽媽轉過頭去,之後就再也沒有望向我),不過,我發現我想起的並不是抵達監獄的事,而是我們有這麼多時間可以坐在這裡好好思考。我想的也不是法官以震耳欲聾的聲音宣判我的徒刑有多少年,更不是天底下完全沒有人相信我是無辜的,所以才落腳於此。不,這一切,我很早以前就放下了。
我不斷回去的是那個夜晚,那個八月的第一個星期六,枷鎖解放的那天。這短暫的自由厚禮足以讓我們帶進墳墓。
我偶爾會沉醉在這個夜晚之中,想想如果事情能有不同的發展,又會如何?如果我跑到柵門邊,還翻了出去。如果我逃了。
也許我會越過三道圍籬,跑下山丘,抵達自由的領土,而我在這個故事裡的戲分就結束了。也許在事情發生之後,一切才會席捲我們,而其他人必須證明這件事發生過,其他人必須負責想起這件事。
因為那天晚上,我們瘋了。我記得我們打架,我們吶喊,我們躲起來,我們用肉身撞向窗戶。我們手邊有什麼,都拿來蹬腿墊高,我們加快速度逃跑,好像只要夠快就逃得出去一樣,但我們逃得還是不夠遠。
那天晚上,我們感受到這六個月、這一年、這十一又半個禮拜、這九百零九天以來從未感受過的情緒。
我們活著。我印象中是如此。我們還活著,而我們在黑暗裡搞不清楚東西南北,所以不曉得自己距離結束只有一步之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