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Step Toward Falling
| 作者 | Cammie McGovern |
|---|---|
| 出版社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 商品描述 | 在我們墜落之前:共鳴推薦宋怡慧(新北市立丹鳳高中教務主任)李崇建(教育工作者、作家)凌性傑(作家、教師)羅怡君(刺蝟媽媽)(親職溝通作家) 如果青春是在認同中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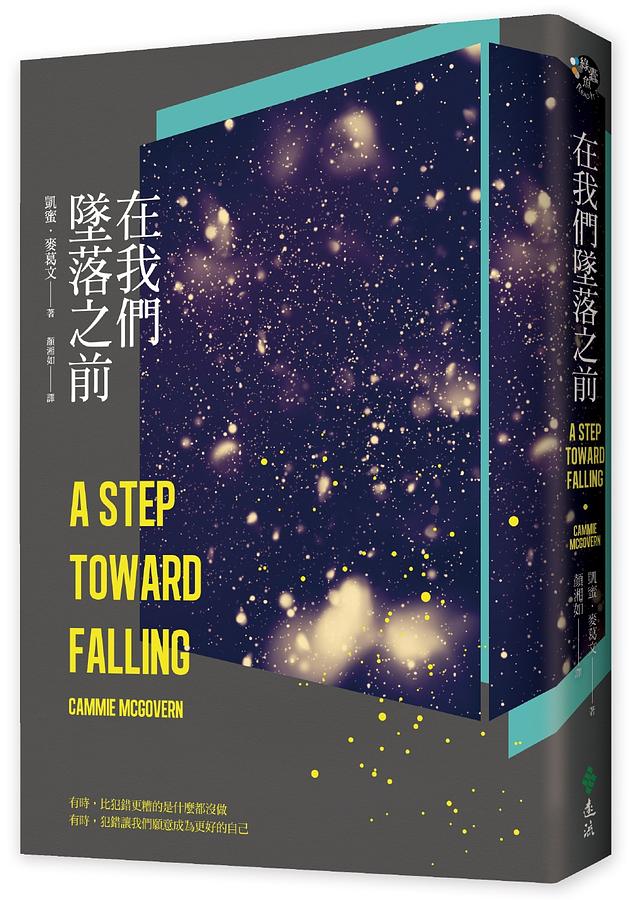
| 作者 | Cammie McGovern |
|---|---|
| 出版社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 商品描述 | 在我們墜落之前:共鳴推薦宋怡慧(新北市立丹鳳高中教務主任)李崇建(教育工作者、作家)凌性傑(作家、教師)羅怡君(刺蝟媽媽)(親職溝通作家) 如果青春是在認同中迷 |
內容簡介 熱血高中女生vs. 帥氣足球校隊男孩,還有一個身心障礙女孩以行動的勇氣點燃青春的正義之心!從誤解到理解、從同理到接納,是最可貴的學習之路 艾蜜莉是個充滿正義感的高中女生,她和好友在校內發起「青年行動聯盟」,高聲呼籲「反對暴力」。有個夜晚,艾蜜莉在足球場的陰暗角落目睹一樁暴行,但她終究未能鼓起勇氣伸出援手,默默掉頭離去。接著,另一名目擊者——高大壯碩的足球校隊隊員路卡斯——在黑暗中快步離開現場。被害者白琳達是同校特教班學生,她純真友善、熱情開朗,直到這樁暴行使她變得膽怯退縮,如驚弓之鳥。艾蜜莉和路卡斯未能「見義勇為」,受到校方懲罰,到社福中心擔任志工,協助身心障礙青少年。當志工的經驗對艾蜜莉和路卡斯有何影響?是否能讓他們省思自己犯的「錯誤」?艾蜜莉和路卡斯該如何彌補白琳達受到的傷害,使她願意重新接納他們兩人?
各界推薦 ◎聯合推薦新北市立丹鳳高中教務主任/宋怡慧教育工作者、作家/李崇建作家、教師/凌性傑親職溝通作家/羅怡君(刺蝟媽媽) 如果青春是在認同中迷失、又重新找到自己定位的過程,《在我們墜落之前》給予每個讀者力量,只要願意肯定自己,終將創造獨一無二的精采人生。--新北市立丹鳳高中教務主任/宋怡慧 本書書寫少年在人際、環境、理想與價值觀的衝突,以及成長歷程的刻畫。我非常推薦這本書。--教育工作者、作家/李崇建 本書以溫柔又不脫現實的精采故事,向父母示範如何觸碰孩子內心難以言喻的心情與成長過程的挑戰。--親職溝通作家/羅怡君(刺蝟媽媽) 國際好評 這是一本探討脆弱與力量、挫敗與療癒之書。故事中的青少年審視心中的成見並勇於突破自我,讓讀者為他們的努力喝采。——《美國童書中心告示牌月刊》 作者並不刻意迴避困難議題或過度美化,而讓讀者明白:「正常者」與「障礙者」並非截然不同,因為我們同而為「人」。——《出版人週刊》 人性共通的情感與共同面對的挑戰,讓本書的幾位主角得以跨越性別、階級和智力的分界。這是一本優美而寬厚之書,藉由兩個不同特質的少女和引人入勝的情節帶出珍貴的啟示,深深打動讀者。 ——《紐約時報》 作者長期和身心障礙孩童相處,讓這個故事充滿動人光彩且鼓舞人心。——《美國圖書館協會書單雜誌》 很難不愛上這本書。這個故事描繪青少年的內心世界,讓讀者感受到滿滿的希望與療癒。——新書訊息網站BookBrowse.com 《在我們墜落之前》提出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如果你目擊一場暴行,你會怎麼做?——亞馬遜網路書店讀者Christina 我在這本書讀到豐富的訊息:關於原諒、接納、發掘真相和療癒。 ——亞馬遜網路書店讀者Mass Reader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凱蜜.麥葛文(Cammie McGovern)已出版幾本小說,其中,書寫身心障礙者的青少年小說《Say What You Will》叫好叫座,得到廣大迴響,促使她寫下《在我們墜落之前》。麥葛文有三個兒子,長子是自閉兒,因而格外關注身心障礙者,並成為社福機構「全人兒童」(Whole Children)的共同創辦人之一,為身心障礙青少年規劃課外活動,讓他們學習生活技能,且有更多人際互動的體驗。■譯者簡介顏湘如美國南伊利諾州大學法文系畢業,現為自由譯者。譯著包括《別相信任何人》、《龍紋身的女孩》、《祕史》、《梅岡城故事》、《守望者》等數十冊。
| 書名 / | 在我們墜落之前 |
|---|---|
| 作者 / | Cammie McGovern |
| 簡介 / | 在我們墜落之前:共鳴推薦宋怡慧(新北市立丹鳳高中教務主任)李崇建(教育工作者、作家)凌性傑(作家、教師)羅怡君(刺蝟媽媽)(親職溝通作家) 如果青春是在認同中迷 |
| 出版社 /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 ISBN13 / | 9789573278894 |
| ISBN10 / | 9573278898 |
| EAN / | 9789573278894 |
| 誠品26碼 / | 2681384834009 |
| 頁數 / | 272 |
| 開數 / | 25K |
| 注音版 / | 否 |
| 裝訂 / | P:平裝 |
| 語言 / | 1:中文 繁體 |
| 尺寸 / | 20.9X14.8X2CM |
| 級別 / | N:無 |
內文 : 1
白琳達
最近我都在看《傲慢與偏見》。不是綺拉.奈特莉主演的新版電影,而是柯林.佛斯主演的舊版影集,要看比較久。這是婆唯一一套盒裝DVD,但她說沒關係,反正她也只需要這一套。婆愛死了達西先生,也就是柯林.佛斯,我也一樣。
這陣子我沒去上學,整天都在看這套片子。
我上的是威徹斯特高中,但今年就要畢業了,也就是說應該要很開心才對。今年開學第一天,媽播了一首歌叫〈期待〉,因為她想讓我別那麼緊張。歌手不停重複唱著:「留下來吧,為了那些美好的往日。」我心想,也許我該留在家裡,別上校車,因為有時候我並不覺得學校生活是美好的往日。
但我還是上了校車,然後坐到我的老位子上,也就是司機背後的第一個座位。這幾年換了司機,現在不是那個叫卡爾的男司機,而是一個叫蘇的女司機。儘管如此,我從沒換過座位,始終坐在司機正後方。只要坐在司機後面,車上就沒有壞學生敢取笑我,或是假裝跟我好,卻把掉在髒地板上的糖果拿給我吃。坐在司機後面就代表周圍坐的大都是七年級學生,他們心裡也害怕。
我已經上學這麼久,應該不再害怕才對,但有時候還是怕。開學前一天婆會提醒我,學校裡有一些我喜歡的東西,譬如在行政辦公室負責紙張回收和分發郵件的工作。婆還列出所有我喜歡的老師,像是蘭妲、凱拉和寇佩老師。想到這些,我通常就會想起其他喜愛的事物,像是學校餐廳裡的柑橘、藝術品展示櫃,還有聽樂隊練習。婆比媽更知道怎麼讓我想起這些事情,媽也很努力,只是有時候會忘東忘西。
如今一切都變了。現在婆試著要幫我忘記,她不再鼓勵我上學,而是讓我每天留在家裡看《傲慢與偏見》。要是媽問她什麼時候讓我回學校,婆就說:「拜託,羅蘭,就隨她吧,至少我們知道她在這裡很安全。」
通常媽和婆不會在我面前吵架。通常她們也不怎麼吵架,因為媽有些缺陷還有憂鬱症。媽會儘可能幫我,但我現在需要的已經不多,所以她能幫的也很少。譬如,我以前會自己做午餐,放進午餐袋裡,不過那是我還要上學、吃午餐時的事。現在我已經不去學校,也就不用準備午餐了。
我看著螢幕裡,珍因為賓利先生一句話也沒說就離開鎮上而強忍著不哭,光是看著她忍住淚水,我就哭起來了。沒想到連《傲慢與偏見》裡的人也這麼壞,都不顧別人的感受。平常我喜歡把自己想像成伊莉莎白,但今天閉上眼睛,卻覺得自己像珍,本以為交到了朋友,結果卻不是這麼回事。
有時候我做的事會讓人感到不舒服。譬如,要是我太常說起柯林.佛斯,老師們就會不舒服。有一次,我的語言治療老師蘭妲就跟我說了她不舒服的感覺:「我聽柯林.佛斯都聽煩了!我又不認識他。他住在很遠的地方,我不想再談他了!」
我們倆都笑起來,但其實我並不覺得她的話有趣。我無法想像厭煩柯林.佛斯的感覺,因為我愛他,有時候當他從電視螢幕裡看著我,我幾乎可以肯定他也愛我。
我知道這種話不能說出來,不然別人會很不舒服,以為我瘋了。他們會說我從來沒見過佛斯先生,也就是說他不可能愛我。我只好轉述媽跟我說的話:愛是一種感覺,你不一定要親吻你愛的人,「有時候你就只是愛他們而已。」她是這麼說的。
當我問她:「那是不是表示他們也愛我?」她說:「當然了,白琳達。大家都愛你。」
我想她指的主要是學校的老師,但柯林.佛斯應該也可以包括在內。當他看著我,我就能感覺得到。真的。我心裡很清楚。
我的語言老師蘭妲卻不這麼想:「他是一個角色,他不是真的。他是電視上的人,但電視不是真的。」
我不知道該怎麼回答。對我來說他是真的,那他不就是真的了嗎?
我不是一直在看《傲慢與偏見》,有時候也會看不同的老電影。我很喜歡《亂世佳人》和《真善美》,可是不喜歡看到瑪麗亞和上校接吻,因為他太老了,看起來像她爸爸。我也喜歡莉瑟和羅夫合唱那首歌,只可惜最後發現羅夫是納粹。看完以後,我在心裡把他變成不是納粹,並讓他們結婚,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亂世佳人》裡的郝思嘉也一樣。一開始她愛著艾希禮,這個人名字像女生,卻是個男的。艾希禮人非常好,但不愛郝思嘉。後來她遇見白瑞德,他是個危險又帥氣的人,而且對她一見鍾情。我憑著想像讓艾希禮改變心意,決定要愛郝思嘉,那麼她身邊就有一個熟悉又可靠的人了。她不能依靠白瑞德。他雖然很讓人心動卻不可靠。有時候讓人心動的男生正是最要不得的。
關於讓人心動卻不可靠的男生,我是從其他電影知道的。對這種人要小心,因為他們多半也都很帥,所以會讓人傻傻分不清。
「像這種男人,有些我會躲開,他們實在太帥了,害我連話都說不出來。」媽說:「是真的,我整個口乾舌燥,好像有人在我嘴裡塗滿膠水一樣。」
這種感覺我知道,我每次看柯林.佛斯演的《傲慢與偏見》都是這樣,根本說不出話來。有時候想不眨眼睛盯著看,但也辦不到。我覺得頭暈暈的,媽說她有一次約會也是這樣,當她站起來要去洗手間,卻往後跌坐在椅子上,好不尷尬。
「我要是喜歡那個男人就會這樣。」媽說:「笨手笨腳的,很難讓人有好感。」
這我懂。不只是看柯林.佛斯,我在現實生活中也有過同樣經驗。每次和莫迪在一起,我就有這種感覺。有時候甚至只要離他近一點,就覺得既想笑又想哭,不然就是心臟好像快要爆炸了。
我會覺得不太對勁,好像心臟病發作似的,只不過每次都只有看到他才會這樣,所以不是真的心臟病。這是愛。我跟媽說起他的事,媽是這麼說的。「你戀愛了,白琳達,那是很美好又特別的感覺……」
她沒有說這種感覺不好或不對,甚至沒有說她應該要說的話:「你要小心點,白琳達。」而是說:「你和其他人一樣都值得人愛。」這讓我混淆了好一陣子,以為莫迪或許也愛我。
艾蜜莉
關於路卡斯──以及我們為何受罰──的事實有點複雜,我不太願意承認,尤其不想對李察承認。他總是痛恨他所謂「足球隊所造成以性別來規範的階級結構」,我不是很明白他的意思,但有一部分不言自明。足球校隊在校內權力太大,特別是今年戰績如此輝煌。我看過自助餐阿姨揮揮手就讓他們過去,端了整盤食物,卻一毛錢也不用付。我看過一些無名小卒替他們買汽水、背書包,一切都只為了贏得某位球員三秒鐘的肯定。
李察認為我們這群朋友不一樣,但其實不然。我們或許沒有卑躬屈膝去吸引校隊球員的注意,但每天午餐時間仍會盯著他們那一桌看上好一會。我們看到了問題,並不代表我們就沒有問題。
路卡斯從未和我談過發生在白琳達身上的事,因此我不知道他是否也和我一樣內疚,或者他覺得受到不公平的懲罰。我猜應該是後者──發生那種事他當然感到遺憾,但錯不在他。至少,他八成認為我的責任比他大,這或許是事實,只是我沒有向任何人承認過。
我還是難以理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表面上看來,事情很簡單。三星期前,我和四個最要好的朋友:李察、巴瑞、韋玲、康蒂絲,去看我們的主場賽。平常我們並不怎麼迷足球,但今年每個人都會去看主場比賽。隨著一場場勝利,觀眾也一週比一週多。
現在坦承這件事有點蠢,但其實那天晚上我心情很差。過去兩個星期,我一直和一個叫舒茲的男孩互傳一些曖昧簡訊和臉書訊息,自以為是打情罵俏。不料那天他就坐在我們前面第三排,很明顯正在和就讀高二、綁著金髮馬尾的柏薇兒約會。三天前他才傳簡訊跟我說:「我們應該找一天一起做點什麼。」我竟笨得以為他是說我們兩人。但顯然不是,他的意思顯然是:我和別人約會看足球賽時,我們應該坐得近一點,好揮手打招呼。
我倒也不是多愛舒茲,只是當初看他似乎很聰明,也很投入我們青年行動聯盟的活動,不像一般新進成員通常都是對某個議題義憤填膺,對其他議題則意興闌珊。舒茲第一次參加聚會後便留下來,說我們「活動」範圍之廣,又「那麼有理想」,讓他十分欽佩。他有一頭棕色鬈髮,牙齒稍微參差不齊,不知為何看起來更可愛。他告訴我們,支持同志人權並非他的主要訴求,但他當然贊同(說的時候沒有看著李察)。他的主要訴求是環境,他喜歡爬山健行,也希望下一代還有山可爬。這樣的人怎能不令人著迷?接下來一星期,他傳了三次簡訊給我,我又怎能不以為他或許也喜歡我?
但若要老實說,我不得不承認:令我苦悶的與其說是舒茲和一個可愛的二年級生在一起,倒不如說是我對舒茲那麼一長串的誤判。我好像一再重複犯下同樣的錯誤,老是把同學之間的玩笑當成調情,有男生跟我要電話借作業,就以為借作業是藉口,要電話才是主要目的。
這有一部分得怪李察。他總喜歡宣稱每個人至少都有一丁點的同志傾向,也許哪天就會忽然迷戀上他。假如和那個四分衛萬人迷卡萊特同坐在辦公室等著領遲到證明,他就會說他們的手毛互相吸引。他也知道什麼都不會發生,卻仍老想著這些時刻。「手毛不會說謊,或者應該說它沒辦法說謊,因為它沒有獨立的大腦,只有直覺。」
他覺得這樣很有趣。誰也不認為卡萊特會奇蹟似的出櫃,和李察兩人手毛水乳交融,但是當我試圖作美夢,開玩笑的說:「舒茲好像想約我出去,只是太害羞了。」才過一星期,卻得坐在他身後眼睜睜看著他有多不害羞,真教人傷心。李察什麼也沒說,這讓我覺得更可悲──如果還能更可悲的話。忽然間,周遭的人好像連呼吸都小心翼翼。
這是我對當晚發生的事所做的解釋之一,不是找藉口或為自己辯護,只是為了弄清楚我怎能讓自己這麼失望。中場休息快結束時,我悄悄溜到小吃攤去買汽水,回座位途中卻哭了起來,那是荒謬、尷尬、自憐的淚水。我從未當眾哭過——從來沒有,自然不想讓朋友看見,便繞到觀眾席後面,心想只要痛快的哭一下,發洩發洩,下半場就沒事了。
後來我迷路了,跑到球員的中場休息室附近。太遲了,五分鐘前球員們便在如雷的掌聲中上場。我們落後七分,這對我們來說是有差別的。我們已經太習慣於大幅領先,觀眾不禁焦慮得吶喊頓足。
儘管噪音喧天,我卻還是聽到觀眾席底下有個奇怪的聲音。聽起來像是動物,可能是小狗掉下去,卡在觀眾席下方的網格。這當然說不通,但聽起來很像。觀眾席底下很暗,只透出一絲絲細微光線,眼睛需要一點時間才能適應。起初我什麼也看不見,便靠近一些。一定是狗,我心裡暗想。可以聽到一陣唧唧哼哼的聲音,然後慢慢的,在黑暗中,出現了兩個人影。我認出其中一人。那是白琳達,幾年前我在兒童劇場課認識的女孩,她緊緊貼靠圍籬,前面站著一個男孩。她看似頭髮被扯住,衣服也撕破了。有那麼一刻我想到的是:她被鐵絲網卡住了,男孩在幫她脫困。
否則怎麼也說不通。最後一次見到她時,她在表演《小紅帽》。
隨後我認出了那個男孩是卜瑞奇,曾有一次在校內遭警察逮捕,押上警車帶走。原因始終不明,但流言紛紛,多半與毒品有關。知道這些事讓眼前的景象更駭人,而且不知為何,也更難理解。等等,我不斷想著,等一下。
我應該大聲喊出這句話才對,我現在知道了。
我應該大聲喊出任何一句話,明確表達出這景象不對勁。我認識白琳達,只是我的大腦無法處理眼睛所看到的:她緊靠圍籬,無力的站在他後面。他們不可能是一對,甚至不可能是朋友。我應該喊她的名字,儘管過去三年我沒有跟她打過一次招呼,我也應該高喊:「白琳達,是你嗎?」但我沒有。那一刻我震驚得說不出話來,事後也幾乎毫無記憶。我知道在某個時間點,有個足球員從更衣室跑出來,當時我想必吃了一驚而暫時脫離驚恐狀態。也或許我心想:可以離開了,因為現在有他在,他會處理。說真的,我不記得了。
我知道自己踉踉蹌蹌走出觀眾席下方,眼前是滿場的歡聲雷動與炫目光線。我知道我找到一位女老師叫艾芙蕊,她繫了一條絲巾、戴著絨絨球耳環,圈起手掌放在嘴邊高喊著:「防守加油!」我碰碰她的手肘,說道:「觀眾席下面出事了!」我們身後的歡呼聲更加響亮。
「什麼?」她喊道。
「出事了。是個女生。在觀眾席下面。」當時我的心跳比我的嗓門還大聲。
忽然間,看台上所有人都站起來大聲尖叫。後來我才知道,我方截球成功,還帶球衝向四十五碼線。我們反敗為勝。每個人都樂瘋了,又是尖叫又是擁抱又是頓腳。
接著我看到剛才在觀眾席下面的那個足球員慢跑進場,不由得大大鬆了口氣。我暗忖:他處理好了,他阻止了本來可能發生的事。
我坐下片刻好讓心跳放慢。當心跳和緩後,我走回觀眾席另一端的原來座位,看見小吃攤旁的停車場有一輛警車閃著紅燈。起先很是驚訝,但想到它代表的意義便隨即安心:沒錯,那個足球員報警了。
當天晚上我沒怎麼睡,也就是說,隔天早上看報紙時心神很不安寧。我在第四版看到一小篇報導,標題寫著「警方因意外事故來到高中足球賽現場」。沒有提到任何學生的名字,也沒有太多相關細節,但我一看到標題就崩潰了,立刻向父母坦白事發經過。「我看見了。我是不小心撞見的,也不知道怎麼回事,我就整個人呆住了,什麼事也沒做。」
爸媽連忙出言安慰。「親愛的,你是害怕自己會有危險。你只是順應本能,誰也不能怪你。」
「當然可以怪我。」我對母親說。我愈想愈覺得自己的反應很差勁。「我沒有幫她,我跑走了,留給另一個人去處理。真是差勁。」
母親試圖與我爭辯,但她能說什麼呢?我確實什麼也沒做。最後她只能緊握我的手說:「總之呢,謝天謝地,有另外那個男孩在。聽起來那個女孩應該沒事,我們大家也都該把這件事放下。沒事的,小莉。下次就不會這樣了。」
我無從知道白琳達是否真的沒事,因為我沒在學校裡見到她,但話說回來,我們走的路徑幾乎從無交集,所以這或許並不代表什麼。事發後一整個星期,我不停的在學校裡找她,心想她大部分時間應該都待在生活技能教室,便不時打那兒經過,但始終沒見到她。有一天早上,倒是看見她幾個同學穿著圍裙在開玩笑。其中一人剛好抬起頭看見我,我便問:「白琳達在嗎?」
「不在,」他回答道:「我們很久沒看到白琳達了。」
要想知道她好不好,還能怎麼做呢?那天我沒去吃午餐,而是站在體育辦公室外,研究足球校隊的名單。我想知道是哪個球員救了她。我沒看清他的臉,卻記得他的球衣號碼,原來是路卡斯,我們從未同班過,除了他的大塊頭之外,我對他毫無所悉。記得有人說過他穿十六號球鞋,必須特別訂製,因為這種鞋子並未量產。
當天放學後我被叫到輔導室,輔導老師告訴我再也無須暗自受罪惡感折磨,應該要說出來(而且是和各個專業人士廣泛討論)。直到此時我才知道:我並不孤單。原來路卡斯也同樣袖手旁觀。
又過了一星期才總算得知事情的全貌,但真相卻令人難以置信。沒想到是白琳達救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