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古董 (新版)
| 作者 | 唐魯孫 |
|---|---|
| 出版社 | 大地出版社有限公司 |
| 商品描述 | 老古董 (新版):【暢銷數十年,全新改版】歷史學者、美食評論家逯耀東先生作序推薦【內容簡介】本書專講掌故逸聞,作者對滿族清宮大內的事物如數家珍,而大半是親身經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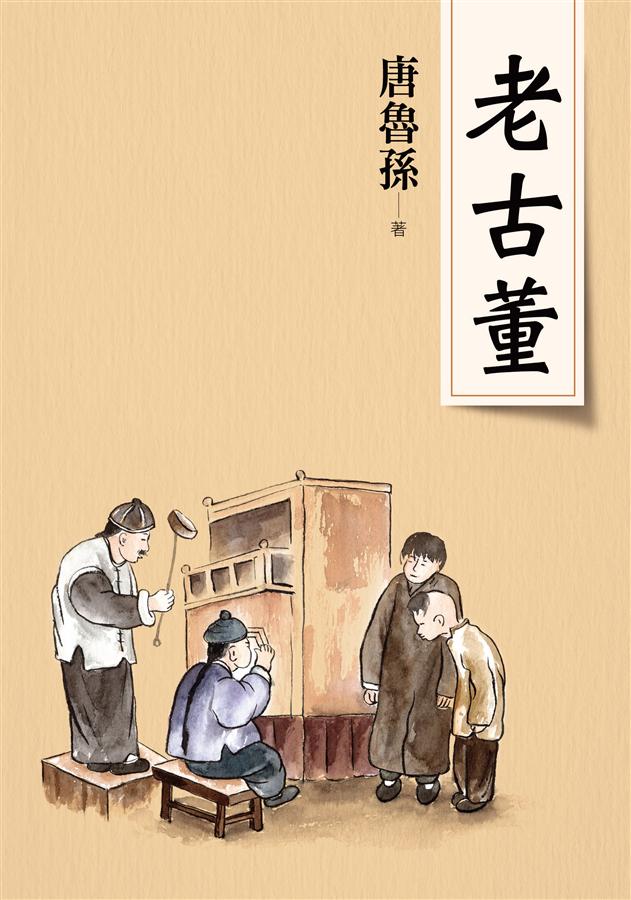
| 作者 | 唐魯孫 |
|---|---|
| 出版社 | 大地出版社有限公司 |
| 商品描述 | 老古董 (新版):【暢銷數十年,全新改版】歷史學者、美食評論家逯耀東先生作序推薦【內容簡介】本書專講掌故逸聞,作者對滿族清宮大內的事物如數家珍,而大半是親身經歷, |
內容簡介 【暢銷數十年,全新改版】 歷史學者、美食評論家逯耀東先生作序推薦 【內容簡介】 本書專講掌故逸聞,作者對滿族清宮大內的事物如數家珍,而大半是親身經歷,所以把來龍去脈說得詳詳細細。本書有歷史、古物、民俗、掌故、趣味等多方面的價值,更引起中老年人的無窮回憶,增進青年人的知識。
作者介紹 唐魯孫唐魯孫,本名葆森,魯孫是他的字。民國前三年九月十日生於北平。滿族鑲紅旗後裔,是清朝珍妃的姪孫。畢業於北平崇德中學、財政商業學校。擅長財稅行政及公司理財,曾任職於財稅機關,對於菸酒稅務稽徵管理有深刻認識。民國三十五年臺灣光復,隨岳父張柳丞先生來臺,任菸酒公賣局秘書。後歷任松山、嘉義、屏東等菸葉廠廠長。當年名噪一時的﹁雙喜﹂牌香煙,就是松山菸廠任內推出的。民國六十二年退休,計任公職四十餘年。先生年輕時就隻身離家外出工作,遊遍全國各地,見多識廣,對民俗掌故知之甚詳,對北平傳統鄉土文化、風俗習慣及宮廷秘聞尤其瞭若指掌,被譽為民俗學家。再加上他出生貴冑之家,有機會出入宮廷,親歷皇家生活,習於品味家廚奇珍,又見多識廣,遍嘗各省獨特美味,對飲食有獨到的品味與見解。閒暇時往往對各家美食揣摩鑽研,改良創新,而有美食家之名。先生公職退休之後,以其所見所聞進行雜文創作,六十五年起發表文章,民俗、美食成為其創作基調,內容豐富,引人入勝,斐然成章,自成一格。著作有《老古董》、《酸甜苦辣鹹》、《天下味》等十二部(皆為大地版)量多質精,允為一代雜文大家,而文中所傳達的精緻生活美學,更足以為後人典範。民國七十二年,先生罹患尿毒症,晚年皆為此症所苦。民國七十四年,先生因病過世,享年七十七歲。
產品目錄 饞人說饞 逯耀東 007 序 陳紀瀅 014 唐魯孫先生小傳 018 天寒數九話皮衣 020 可抓住了小辮子 034 湯婆子的種種 036 肥得籽兒、刨花、皂莢 040 看了兩齣過癮的戲 044 北平精巧的絨花手藝 047 杆兒上的 051 迎春話水仙 056 清朝宮廷童玩 061 北平年俗:白雲觀順星 065 吉羊 068 昔日最高學府國子監 073 中元普渡話盂蘭 078 從杜夫人義演談談《硃砂痣》 083 潭柘 086 清宮過端陽 091 皇史宬石室金匱 097 清代皇陵被盜述聞 101 慈禧寵監李蓮英 114 海甸之憶 121 北洋時代上早衙門 128 北平天橋八大怪 133 離不開醒木、扇子、手帕的評書 140 西鶴年、同仁堂 150 臺南民俗展婚禮服飾談 162 猴年來了 164 姑且妄言狐仙事 177 冬雪瑣憶 182 敬悼平劇評人丁秉鐩 189 也談痰盂 191 年畫瑣憶 195 清宮年事逸聞 200 我看《乾隆皇與三姑娘》 210 想起了長桿旱煙袋 213 我的床頭書 216 閒話轎子 218 中國瑰寶萬里長城 225 水煙袋 230 春明燕九話白雲 238 故都梨園三大名媽 247 後 語 255
| 書名 / | 老古董 (新版) |
|---|---|
| 作者 / | 唐魯孫 |
| 簡介 / | 老古董 (新版):【暢銷數十年,全新改版】歷史學者、美食評論家逯耀東先生作序推薦【內容簡介】本書專講掌故逸聞,作者對滿族清宮大內的事物如數家珍,而大半是親身經歷, |
| 出版社 / | 大地出版社有限公司 |
| ISBN13 / | 9789864023264 |
| ISBN10 / | 9864023268 |
| EAN / | 9789864023264 |
| 誠品26碼 / | 2681845066000 |
| 頁數 / | 256 |
| 開數 / | 25K |
| 注音版 / | 否 |
| 裝訂 / | P:平裝 |
| 語言 / | 1:中文 繁體 |
| 級別 / | N:無 |
最佳賣點 : 【暢銷數十年,全新改版】
歷史學者、美食評論家逯耀東先生作序推薦
內文 : 唐魯孫先生小傳
唐魯孫,本名葆森,魯孫是他的字。民國前三年九月十日生於北平。滿族鑲紅旗後裔,是清朝珍妃的姪孫。畢業於北平崇德中學、財政商業學校。擅長財稅行政及公司理財,曾任職於財稅機關,對於菸酒稅務稽徵管理有深刻認識。民國三十五年臺灣光復,隨岳父張柳丞先生來臺,任菸酒公賣局秘書。後歷任松山、嘉義、屏東等菸葉廠廠長。當年名噪一時的「雙喜」牌香煙,就是松山菸廠任內推出的。民國六十二年退休,計任公職四十餘年。
先生年輕時就隻身離家外出工作,遊遍全國各地,見多識廣,對民俗掌故知之甚詳,對北平傳統鄉土文化、風俗習慣及宮廷秘聞尤其瞭若指掌,被譽為民俗學家。再加上他出生貴冑之家,有機會出入宮廷,親歷皇家生活,習於品味家廚奇珍,又見多識廣,遍嘗各省獨特美味,對飲食有獨到的品味與見解。閒暇時往往對各家美食揣摩鑽研,改良創新,而有美食家之名。
先生公職退休之後,以其所見所聞進行雜文創作,六十五年起發表文章,民俗、美食成為其創作基調,內容豐富,引人入勝,斐然成章,自成一格。著作有《老古董》、《酸甜苦辣鹹》、《天下味》等十二部(皆為大地版)量多質精,允為一代雜文大家,而文中所傳達的精緻生活美學,更足以為後人典範。
民國七十二年,先生罹患尿毒症,晚年皆為此症所苦。民國七十四年,先生因病過世,享年七十七歲。
天寒數九話皮衣
寶島臺灣夏季雖然鬱熱蒸薰,讓人喘不過氣來,可是到了隆冬三九,大陸正是呵氣成雲,滴水成冰,凍得人哆嗦發抖,縮手頓腳的時候,臺灣如果沒有寒流來襲,那簡直跟大陸春秋天一樣的令人神清氣爽舒適異常。三十年前臺灣剛剛光復,臺北中華路一帶還沒有改建中華商場之前,在鐵路的兩邊的柵戶地攤上,偶或還能夠發現男裝女裝的皮襖皮大衣待價而沽,想必都是大陸來臺士女們帶來壓箱底的皮貨。時光荏苒,一晃三十多年,近十多年來要想在中華商場或是萬華一帶殘存的估衣鋪尋摸點舊皮貨,那簡直如大海撈針難上加難了。
臺灣的隆冬歲臘,若是碰上巨大寒流接踵而來,照樣寒飆凜冽,清滄襲人。走在大街小巷,青年男女雖然很少有穿著皮衣外出的,可是高年血氣兩衰的,穿上皮襖來擋擋寒氣的也還頗有其人呢!
記得三十九年耶誕夜,中英尚未斷交,淡水英國領事館特地舉行耶誕晚會。天剛傍晚,忽然下起小冰珠來,雖然落地就化,可是西北風兒吹颳臉上居然有點刺痛,這樣冷的天氣在臺灣實在太難得了,筆者那天特地把壓箱底的皮大衣拿出來穿上赴宴亮亮相,同時也趁此機會讓皮衣透透風。想不到各國淑女名紳都是紛御狐裘貂襖前來與會,我方應約來賓浦薛鳳、任顯群兩位也是穿了皮氅來的,區區這件皮大衣總算不枉飛天跨海萬里關山帶到臺灣,居然也派了一次用場。
當年在大陸有些講究穿皮的人家,一到冬天先穿小毛,再冷換穿大毛,先穿彎毛後穿直毛。清朝對於什麼節令穿什麼皮毛都有一定之規的,《宮門抄》先釐定日期,昭告臣民,到期大家一律改穿,名為換季。行走宮廷之間的文武官員,一律恪遵,不容稍有混淆,否則是要受處分的。
所謂彎毛也就是羊皮,一般人都知道老綿羊皮是最普羅化的皮襖了,白渣兒統子,不吊布面,不釘鈕扣,用一條搭膊(布帶子華北叫搭膊)往腰裡一繫,雖然不雅觀,可是溫暖俐落,是一般賣力氣朋友們冬季的恩物。羊皮是西北特產,分西口貨、北口貨兩種,其中以寧夏產品最好,毛頭細密而長,質地輕柔而暖,高級品叫「蘿蔔絲灘皮」,毛穗有九道彎,可想羊毛有多長啦!還有一種特級品「竹筒灘皮」,整件長皮襖統子,能捲在粗僅盈握的竹筒子裡,這種皮統子是如何的輕軟名貴,就不難想像了。
「黑紫羔」也屬於羊皮的一種,毛頭黑亮,在日光底下一照,表裡都泛出灩灩深紫顏色。青海、寧夏、新疆都出產紫羔,其中以新疆庫車的最著盛名,毛頭細短,捲曲韌密。清朝定制凡是列入品級的職官,逢到國殤,臨哀弔祭都要反穿紫黑外褂參加叩拜,因此大家把黑紫羔視為不祥的喪服,就是講究收藏皮貨的人家,也不願意收藏黑紫羔的,一遇大殤全是現買現做,除服賞人,皮貨莊碰上了這種好生意,染色羊皮就藉此大批出籠,由於早年染色技術欠佳,霜雪一沾,順手掉色,這種假紫羔當然就更沒有收藏價值了。當年有句話是「少不了的金絲猴,不上譜的黑紫羔」,凡是收藏家一定要有金絲猴皮貨才算搜集齊全,可是沒有紫羔。
金絲猴的毛有一尺多長,五色斑斕,隱現金光,大都是拿來做成坐褥,鋪在炕上取暖之用。傳說當年北洋軍閥中有位土包子師長,拿金絲猴做了一副套,因為底毛太長,只好捲在筒裡頭,走起路來自然顯得鼓鼓揣揣。有一次他去中海居仁堂參加直奉軍聯席會議,會場戒備森嚴,門衛看他軍服臃腫步履蹣跚,堅不放行,後來弄清楚此公是穿了皮套的原因,從此就被大家封為套師長矣。
說到黑紫羔還有一樁故事。民國初年北平東交民巷法國公使館(當時不叫大使館)有幾位法國員司忽然對於黑紫羔發生興趣,在北平各大皮貨莊大量搜購。紳士們做帽子、換大衣領子,淑女們做反穿大衣、手籠子,一時間供不應求,於是有少數商業道德差的皮貨莊就把沙羊皮拿來冒充。這種染過色的沙羊皮乍看很像紫羔,可是宜於遠觀,不能近覷,要是走近仔細的瞧,黑則黑矣,可是黑不泛紫,光芒更差。還有一樁事,令人膩煩,縱然是反穿,可是從雪地一走進有暖氣的屋子,立刻有一種輕微的臭味,因此熱鬧一陣子之後,穿紫羔的風氣也就煙消霧散啦!聽說蓋仙夏元瑜兄染皮子的手藝別有竅門,染出來的假紫羔可以亂真,可惜當年皮貨莊那些皮匠們不認識他。
「珍珠毛」又叫「藏羔」,顧名思義是出在西藏,這種羔皮是胎羊已經生毛,還未等到小羊降生,就把母羊剖腹取出來的,取胎羊時間要掐得準,太早僅生茸毛,稍晚毛長不曲,都不值錢,而等茸毛鬈起像一粒粒米星珠子似的取胎才算上品。珍珠毛有黑白兩種顏色,黑珠羔產量少,所以兩者價錢相差很多。大陸在涼秋九月,已涼天氣未寒時穿珍珠毛,為期不過短短十來天,而且剖腹取胎過分殘忍,有些人寧可穿襯絨袍也不願意穿珍珠羔,就是這個道理。可是一般講究玩皮貨的人最少也要有一件坎肩或馬褂來聊充一格,才算皮貨收齊全了呢!
筆者小時候一到冬令看見人家穿著皮襖,就眼熱得不得了,可是恪於家規,小孩子不到成年,一律不准穿皮衣。一則是怕從小養成奢靡浮誇的心理,二則是小孩筋骨不加以鍛鍊,將來外出就業闖南蕩北,如何能夠抵禦酷暑奇寒?後來家裡給我做了一件珍珠毛的馬褂,春節外出拜年,穿在身上沾沾自喜得意非凡,後來到了真正有資格穿皮袍子時候,才知道自己當年所穿是麻絲做的品,根本不是什麼珍珠羔呢!
談到直毛皮貨種類可就海了去啦!大概凡是四條腿的動物,都可以拿來做皮襖或褥子墊子等等的。直毛最便宜的要算狗皮貓皮啦!狗皮雖也能擋寒,可是皮板太硬,而且太重,拿來做褥墊子鋪在炕上取暖倒不錯,喜歡穿狗皮大襖的多半是巡更守夜看家護院的爺們了。貓皮比狗皮輕軟,當年練武的人講究穿貓皮套,什麼理由咱就不得而知了。當年巡更人住的更房,大炕上總要鋪上一張貓皮褥子,據說冬天上夜,少不得要呷兩盅趕趕寒氣,拉拉雜雜剩下點魚頭蝦腦,最容易引來老鼠,鋪上貓皮褥子,鼠類就聞風遠颺不敢輕捋虎鬚啦!所以打更人的窩鋪都少不了一條貓皮褥子,是否靈驗,傳說如此,咱們就姑妄聽之吧!
「貉絨」俗名「關東貉子」,熱河圍場一帶貉子最多,因為它愛吃一種黑殼甲蟲,身上時常發散一種怪味,雖然皮板深厚,毛頭滑潤溫暖,可是當初不能列為皮貨上品。後來歐美各國影劇女星,提倡反穿貉絨女大衣,一陣風行,貉絨的身價,立刻增加百倍。
狼皮有「古狼」、「銀狼」兩種。古狼毛長板重,如果做皮袍穿,暖則暖矣,可是太壓人,所以古狼皮也是拿來做褥墊子的居多。至於「銀狼」又叫「白狼」,取它腋部做皮袍子,那又算是上等皮貨了。
民國初年北平瑞林祥綢緞莊皮貨莊忽然陳列了幾張黑熊皮出售,毛滑絨厚,一色純黑,別無雜毛,據說是長白山獵的大黑熊,跟所謂蒙古褐熊(又叫草地熊)毛頭光彩兩者簡直沒法相比。這種蒙古草地熊經過製皮毛工廠巧手皮毛匠加工整理染黑,皮貨行給它起個名字叫「青克拉楞」,外行人誰也摸不清是什麼獸類,其實就是蒙古狗熊染色。天橋的一般新出道鼓姬都喜歡用「青克拉楞」 做大衣的皮領子,遠看倒也黑而且亮,缺點也是容易掉色,在呵氣成煙的冬天,時常把玉面朱唇染成半邊美人,後來大家也就不敢用來做皮領子啦!當時東北黑熊都是整張硝好運來北平的,尺寸過大,用來做褥子糟蹋材料太可惜,有人索性把它鋪在小客廳地毯上暖腳,反而實惠得用。
「金錢豹」的皮,斑斕耀彩,中國人喜歡拿來做褥子或炕墊,自從北歐幾個國家,有人花樣翻新穿豹皮大衣,再配上豹皮帽子、手籠子,於是豹皮在國際市場大漲,直到目前豹皮大衣在歐洲價錢還是很貴呢!
虎為百獸之王,中國古代王侯爵邸寶座都罩上一張虎皮,三軍統帥的中軍大帳,鹵簿儀鍠赤幘戎冠,主帥座位要披上張虎皮,才顯出鍪鎧儼雅我武維揚。
「灰鼠」又叫青鼠,吉林長白興安嶺都有出產,背灰腹白,跳躍靈活,極難捉捕,淡灰泛白的是上品,深灰色是中品,灰裡泛紅的是次品。全部用灰鼠脊背拼製的皮統子叫灰背,因為耗用灰鼠太多,一襲灰背要比灰鼠價格貴上兩三倍,於是大家都捨不得用灰背做皮襖,做成反穿女大衣,既輕暖又高華,中外名媛都喜歡灰背大衣,尤其北歐有幾個國家,比貂皮還看重呢!
「銀鼠」又名石鼠,也是長白山特產,聚族穴居,因毛色銀白,獵人在冰天雪地極難發現,可是一經踩出銀鼠進出秘道,一網捉個三五十隻並不稀奇,不過銀鼠雖然潔白色純,可惜皮板太薄,過分嬌嫩,在時序輕寒天尚未冷的時候,一襲銀裘穿在風姿綽約、膚如凝脂的閨秀名媛玉體上,真是雍容高雅、卓然不群。
南美洲有一種「兔鼠」,軀體比灰鼠、銀鼠稍大,聽覺視覺異常機警,縱跳如飛,是鼠類最難獵捕的一種,它們生活在一萬英尺以上的高山草叢岩穴裡,毛色藍中帶灰,歐洲年輕貴婦都普遍喜愛它。去年在巴黎女服展示會一件兔鼠女大衣大約是四萬至六萬美金之間,其名貴可見一斑。
「猞猁孫」簡稱猞猁,是介狐鼠之間的一種獸類,產於烏拉山一帶,體態輕盈,能在枯木繁枝揉升跳踉,古人叫它天鼠。它的耳大毛長,形狀跟狐狸近似,所以有人說它是狐,又有人說它是鼠,其實非鼠非狐是另外一種動物(夏元瑜兄說它是東三省產的一種大山貓)。猞猁皮的底板堅柔,鎗子耐磨,是做皮袍子最好的材料。
狐的種類最多,有「玄狐」(又叫元狐,俗稱黑狐)、「青狐」、「白狐」(又叫銀狐)、「火狐」(又叫紅狐)、「沙狐」、「草狐」等。玄狐也是產在東北,極品玄狐純黑發亮面帶白針,到了清朝初年,已經少見。凡是獵到玄狐的,認為是國家祥瑞之徵,十之八九列為貢品,進奉皇家,皇家也只是冬令郊天祝釐時才御玄狐袍褂,賞賚止於親王,親王薨逝,還要立刻繳回,除非奉旨賞還,才敢收歸己有,加以庋藏。所以當年的王公勳戚、顯宦豪門就把玄狐視為無上珍品呢!
「青狐」,遼寧昂昂溪、鐵嶺都是青狐產地,顏色是青裡略帶黑黃,黑多黃少的算是上品,黃多黑少價錢就差了,雖然青狐毛色駁雜,並不十分美觀,可是據說當年努爾哈赤行圍射獵,如果穿了青狐皮氅,一定是出行大吉射必中的,滿載而歸,從此清朝皇帝就把青狐視為祥瑞之兆,後來並且定制,要晉爵貝子貝勒才夠資格賞穿青狐,其重視程度,可想而知。
「白狐」除了輕暖之外,論顏色是潔白如玉、晶瑩勝雪,穿上一件白狐女大衣周旋於明珠金翠、銀衣朱履之間,一枝獨秀確有鶴立雞群的感覺。當年富貴人家,陪嫁妝奩裡,白狐斗篷是不可缺少的,一般人家陪送不起白狐,也要弄一件假白狐天馬皮來充充場面。所謂天馬皮,就是沙狐草狐肚子底下一塊白毛,如果板子拼得巧妙,花頭接得整齊,乍看也分不出白狐天馬來,不過仔細一看,白狐的毛細長而潤,天馬的毛略短而澀,天馬皮最大的缺點是怕樟腦,收藏裝箱時只要撒了樟腦粉或樟腦丸,第二年拿出來穿,天馬皮就由雪白漸漸變成乳黃色啦。
「火狐」又叫紅狐,顧名思義,其紅似火,筆者曾經看見過京南綠林總瓢把子錢三爺子蓮有一件火狐大皮襖,是一對火狐做的皮統子,照此推想狐身長度必定是出號的火狐,才能夠用。火狐紅潤堅重,金縷閃爍,正配綠林大豪的身分。有人說當年北平城郊的四霸天各有一件珍奇的皮襖,可是誰也不願意穿出來亮相,可能言者有據,諒非虛假。
「沙狐」又叫草狐。生於長城各口子,如古北口、冷口砂礫地帶的叫沙狐,生於西北草原的叫草狐。這種狐皮算是最普通的狐皮統子了,唯一的好處是壓風,平素在口裡口外趕火車拉駱駝的朋友,遇到連環旋風騾馬駱駝就地一臥槽,他們跟著把草狐大襖沒頭沒臉往身上一裹,也往牲口堆裡一臥,任憑風怎麼颳。風一停歇,他們站起身來,揮揮沙土,立刻上路,準保毫髮無傷。
狐的種類繁多不算,狐身上用來做皮衣地方也各有名堂。頭部叫「狐頭」,腿部叫「狐腿」,並且有順腿倒腿之分,更有前腿後腿之別。狐的肩臂交接地方叫「腋」,特別柔軟,也就是《史記》上所說:「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可見自古以來,狐腋之裘已經非常名貴了。「狐脊子」這種狐皮取自狐的脊背,毛頭不厚,可是製出統子來特別輕暖。民國二十年筆者在大同,當地趙鎮守使的公子在買賣場買了一件灰狐脊皮統子孝敬老太爺,酒席筵前趙鎮守使一看樂得連喝三飯碗黃酒,據說他們當地鄉風,凡是兒子能買件狐脊子孝敬上人,就表示這家出了一位孝子,而且是事業有成、飛黃騰達啦。狐身上最貴重的是脖子底下一塊叫「狐膆子」,這是狐身上最輕暖的毛皮了。從前家裡如有狐膆子一定先儘老年人穿,年歲未過花甲是不敢隨便亂穿的。
談到「貂」,連國民小學的學生都知道東三省三宗寶:人參、貂皮、烏拉草。本來東北各省松江、合江、安東、吉林、嫩江、黑龍江山區都是產貂地區,凡是越高冷酷寒的地方所產的貂皮越好越能保溫。最大的貂身長也超不過三尺,前後腿不平衡,前腿短後腿長,尾毛像狐狸毛粗而長。東北南邊的安東省產的貂毛根略帶灰白色,獵人叫它「草貂」。吉林、黑龍江更冷地區的貂毛根泛紫名為「紫貂」,毛頭細軟厚密,輕暖保溫,比草貂的價錢約高一倍還多。
獵人捕貂費時費工是一種專門行業,東北土話叫他們「逮老貂的」。每年一交霜降,獵人牽著獵犬,駕著雪橇,馱著冬糧禦寒用具結伴入山,先搭好了木屋,然後分頭踩道。東北早寒,此刻千巖萬壑都是落葉瀰漫,一片枯黃,貂鼠雖不冬眠,可是趁著瑞雪尚未封山的時候,在茂草枯葉之間追奔逐北,尋覓食物。獵人探出貂鼠不時出沒的地方,一一做好暗記,然後設下弩弓套索各式各樣的陷阱。有經驗的獵戶此刻全部按兵不動,因為貂性機警,雖然住在枯木岩洞樹窟裡頭,可是並無長久居住固定的巢穴,一下驚著它們,立刻遠揚不歸,何況天未大冷,皮毛還不夠稠密,他們術語叫狩貂。到了冬至大寒,雪深盈尺,深山溫度均在零下四五十度左右,此刻的貂鼠一個個吃得又肥又壯,不但底絨厚密,油水正足,按著雪痕爪跡,加以捉捕,人人都能飽載而歸。有人說捕貂有用苦肉計的,方法是捕貂的先吃少許信石(砒霜),然後脫去上衣赤身躺在貂鼠出沒的雪地上,貂性仁慈,看見之後必定跑來爬在人身上送暖,獵人乘機就把貂捕獲了。筆者曾經問過東北朋友,他們雖沒捕過貂,可是有親戚朋友是捕貂能手,據說零下四五十度氣候,任何精壯的漢子,就是吃過信石,赤身在雪地也挺不過半小時就凍僵了,就是貂鼠真來覆體也沒力氣捉捕,縱能捉捕也不過是捉個一兩隻,太不划算了。雖有這種傳說,恐怕也不見得有這種事實吧!
貂在直毛皮貨裡,比任何名貴狐皮都輕暖適體不顯臃腫。有一種「貂仁」皮統子,整件皮統都是貂的腦門一塊皮子拼成,穿在身上如同穿十衲棉袍一樣,輕暖不說,而且合身俐落。試想一件貂仁皮統子要用多少隻貂鼠,價錢還能不貴得嚇人嗎?依照清朝制度,文官三品、武官二品以上才有資格穿貂褂子,反穿貂褂子講究「貂翎眼」,這是皮貨莊加工匠人(俗名毛兒匠)挖方做出像孔雀翎眼一樣的花頭,穿在身上顯得特別雍容華貴。京官也有例外,翰林學士雖然頭戴藍頂子,但是可以反穿貂褂,動輒好幾百兩,一般窮翰林這份行頭,如何置辦得起?於是當時有一種「翰林貂」應市,所謂翰林貂實際就是貓皮染的,巧手工匠也能仿造底茸鎗子讓人真假莫辨,這種翰林貂,當年幾十兩銀子就可置備一件,頂翎貂褂,敝佩明璫,周旋於公卿士大夫之間了。到了民國,貂翎眼的外褂雖說英雄已無用武之地,可是拆大改小,一變成了名媛貴婦反穿翎眼的名貴大衣啦。
先師閻蔭桐夫子曾經任駐俄國塔斯干總領事,據說俄國有一種野生「黑貂」比中國的紫貂還要名貴。這種貂又叫「俄羅斯伶鼬」,生在茂密蓊鬱森林高地,它的皮毛濃密柔韌,人用口吹,也不能把毛吹開。而且,保溫力特強,凡是穿戴貂皮衣帽的人,身上沾有雪花,在進屋之前,必須先行拍落,否則立刻溶成一片雪水。俄國人因為黑貂皮價值高昂,於是設法用人工來繁殖,當然皮毛沒有野生貂厚密耐穿,但是價錢仍舊是十足驚人的。
去年巴黎秋冬季時裝展示會,出現了南極貂皮女裝大衣,跟我們東北的紫貂極為近似,時價是四五萬美金左右,真正俄國純野生的黑貂比南極要高三倍還有行無市,一襲女褸要十多萬美金,豈不令人咋舌。
此外專門做皮帽子皮領子的有旱獺、水獺、海獺,三者之中海獺底絨厚、油水足最好,旱獺最差,有一種不拔針的海獺外觀保溫比海龍並不差。那是一些精於鑑賞的人才懂得穿帶針海獺,可稱為物美價廉。另外有一種叫「海留」的,也是水獺一類,顏色絨頭跟水獺彷彿,不同之處就是一個倒毛一個順毛而已。至於海龍顏色比水獺黑亮,而且帶白針,不論是做皮帽子做大衣帽子,的確氣派不同,可是一定要身材高大魁梧的人穿戴起來才合身得體,要是瘦小枯乾的軀幹,戴上海龍四塊瓦的帽子,穿上海龍領子大衣,活像北平有種泥玩藝—小孩躦罎子。不但不相稱,而且看起異常滑稽。
孔庸之先生生前對於各種皮貨都有深入研究,據他說華中西南,到了冬季最冷的時候,也是要穿皮衣禦寒的,不過雨雪爛漫,霧霰霉濕,不是皮板硬化,就是脫線走硝,如果皮衣有這種情形,趕緊送到山西請山西的朋友代為保存一冬兩冬,然後拿出再穿,硬化走硝就全都化為烏有了。有人聽信,照孔先生說法試過,果然靈驗,僵硬皮板柔韌依然。大陸來臺的朋友如果有人帶點皮貨來臺灣,要發現以上情形,將來不妨把這些皮貨送到山西試驗試驗,一定能包君滿意呢!
推薦序 : 饞人說饞—閱讀唐魯孫 逯耀東
前些時,去了一趟北京。在那裡住了十天。像過去在大陸行走一樣,既不探幽攬勝,也不學術掛鉤,兩肩擔一口,純粹探訪些真正人民的吃食。所以,在北京穿大街過胡同,確實吃了不少。但我非燕人,過去也沒在北京待過,不知這些吃食的舊時味,而且經過一次天翻地覆以後,又改變了多少,不由想起唐魯孫來。
七○年代初,臺北文壇突然出了一位新進的老作家。所謂新進,過去從沒聽過他的名號。至於老,他操筆為文時,已經花甲開外了,他就是唐魯孫。民國六十一年《聯副》發表了一篇充滿「京味兒」的〈吃在北京〉,不僅引起老北京的蓴鱸之思,海內外一時傳誦。自此,唐魯孫不僅是位新進的老作家,又是一位多產的作家,從那時開始到他謝世的十餘年間,前後出版了十二冊談故鄉歲時風物,市廛風俗,飲食風尚,並兼談其他軼聞掌故的集子。
這些集子的內容雖然很駁雜,卻以飲食為主,百分之七十以上是談飲食的,唐魯孫對吃有這麼濃厚的興趣,而且又那麼執著,歸根結柢只有一個字,就是饞。他在〈烙盒子〉寫到:「前些時候,讀逯耀東先生談過天興居,於是把我饞人的饞蟲,勾了上來。﹂梁實秋先生讀了唐魯孫最初結集的《中國吃》,寫文章說:「中國人饞,也許北京人比較起來更饞。」唐魯孫的回應是:「在下忝為中國人,又是土生土長的北京人,可以夠得上饞中之饞了。」而且唐魯孫的親友原本就稱他為饞人。他說:「我的親友是饞人卓相的,後來朋友讀者覺得叫我饞人,有點難以啟齒,於是賜以佳名叫我美食家,其實說白了還是饞人。」其實,美食家和饞人還是有區別的。所謂的美食家自標身價,專挑貴的珍饈美味吃,饞人卻不忌嘴,什麼都吃,而且樣樣都吃得津津有味。唐魯孫是個饞人,饞是他寫作的動力。他寫的一系列談吃的文章,可謂之饞人說饞。
不過,唐魯孫的饞,不是普通的饞,其來有自;唐魯孫是旗人,原姓他他那氏,隸屬鑲紅旗的八旗子弟。曾祖長善,字樂初,官至廣東將軍。長善風雅好文,在廣東任上,曾招文廷式、梁鼎芬伴其二子共讀,後來四人都入翰林。長子志銳,字伯愚,次子志鈞,字仲魯,曾任兵部侍郎,同情康梁變法,戊戌六君常集會其家,慈禧聞之不悅,調派志鈞為伊犁將軍,遠赴新疆,後敕回,辛亥時遇刺。仲魯是唐魯孫的祖父,其名魯孫即緣於此。唐魯孫的曾叔祖父長敘,官至刑部次郎,其二女並選入宮侍光緒,為珍妃、瑾妃。珍、瑾二妃是唐魯孫的族姑祖母。民初,唐魯孫時七八歲,進宮向瑾太妃叩春節,被封為一品官職。唐魯孫的母親是李鶴年之女。李鶴年奉天義州人,道光二十年翰林,官至河南巡撫、河道總督、閩浙總督。
唐魯孫是世澤名門之後,世宦家族飲食服制皆有定規,隨便不得。唐魯孫說他家以蛋炒飯與青椒炒牛肉絲試家廚,合則錄用,且各有所司。小至家常吃的打滷麵也不能馬虎,要滷不瀉湯才算及格,吃麵必須麵一挑起就往嘴裡送,筷子一翻動,滷就瀉了。這是唐魯孫自小培植出的饞嘴的環境。不過,唐魯孫雖家住北京,可是他先世遊宦江浙、兩廣,遠及雲貴、川黔,成了東西南北的人。就飲食方面,嘗遍南甜北鹹,東辣西酸,口味不東不西,不南不北變成雜合菜了。這對唐魯孫這個饞人有個好處,以後吃遍天下都不挑嘴。
唐魯孫的父親過世得早,他十六七歲就要頂門立戶,跟外面交際應酬周旋,觥籌交錯,展開了他走出家門的個人的飲食經驗。唐魯孫二十出頭就出外工作,先武漢後上海,遊宦遍全國。他終於跨出北京城,東西看南北吃了,然其饞更甚於往日。他說他吃過江蘇里下河的鮰魚,松花江的白魚,就是沒有吃過青海的鰉魚。後來終於有一個機會一履斯土。他說:「時屆隆冬數九,地凍天寒,誰都願意在家過個閤家團圓的舒服年,有了這個人棄我取,可遇不可求的機會,自然欣然就道,冒寒西行。」唐魯孫這次「冒寒西行」,不僅吃到青海的鰉魚、烤犛牛肉,還在甘肅蘭州吃了全羊宴,唐魯孫真是為饞走天涯了。
民國三十五年,唐魯孫渡海來臺,初任臺北松山菸廠的廠長,後來又調任屏東菸廠,六十二年退休。退休後覺得無所事事,可以遣有生之涯。終於提筆為文,至於文章寫作的範圍,他說:「寡人有疾,自命好啖。別人也稱我饞人。所以,把以往吃過的旨酒名饌,寫點出來,就足夠自娛娛人的了。」於是饞人說饞就這樣問世了。唐魯孫說饞的文章,他最初的文友後來成為至交的夏元瑜說,唐魯孫以文字形容烹調的味道,「好像老殘遊記山水風光,形容黑妞的大鼓一般。」這是說唐魯孫的饞人談饞,不僅寫出吃的味道,並且以吃的場景,襯托出吃的情趣,這是很難有人能比較的。所以如此,唐魯孫說:「任何事物都講究個純真,自己的舌頭品出來的滋味,再用自己的手寫出來,似乎比捕風捉影寫出來的東西來得真實扼要些。」因此,唐魯孫將自己的飲食經驗真實扼要寫出來,正好填補他所經歷的那個時代,某些飲食資料的真空,成為研究這個時期飲食流變的第一手資料。
尤其臺灣過去半個世紀的飲食資料是一片空白,唐魯孫民國三十五年春天就來到臺灣,他的所見、所聞與所吃,經過饞人說饞的真實扼要的記錄,也可以看出其間飲食的流變。他說他初到臺灣,除了太平町延平北路,幾家穿廊圓拱,瓊室丹房的蓬來閣、新中華、小春園幾家大酒家外,想找個像樣的地方,又沒有酒女侑酒的飯館,可以說是鳳毛麟角,幾乎沒有。三十八年後,各地人士紛紛來臺,首先是廣東菜大行其道,四川菜隨後跟進,陝西泡饃居然也插上一腳,湘南菜鬧騰一陣後,雲南大薄片、湖北珍珠丸子、福建的紅糟海鮮,也都曾熱鬧一時。後來,又想吃膏腴肥濃的檔口菜,於是江浙菜又乘時而起,然後更將目標轉向淮揚菜。於是,金霽玉膾登場獻食,村童山老愛吃的山蔬野味,也紛紛雜陳。可以說集各地飲食之大成、彙南北口味為一爐,這是中國飲食在臺灣的一次混合。
不過,這些外地來的美饌,唐魯孫說吃起來總有似是而非的感覺,經遷徙的影響與材料的取得不同,已非舊時味了。於是饞人隨遇而安,就地取材解饞。唐魯孫在臺灣生活了三十多年,經常南來北往,橫走東西,發現不少臺灣在地的美味與小吃。他非常欣賞臺灣的海鮮,認為臺灣的海鮮集蘇浙閩粵海鮮的大成,而且尤有過之,他就以這些海鮮解饞了。除了海鮮,唐魯孫又尋覓各地的小吃。如四臣湯、碰舍龜、吉仔肉粽、米糕、虱目魚粥、美濃豬腳、臺東旭蝦等等,這些都是臺灣古早小吃,有些現在已經失傳。唐魯孫吃來津津有味,說來頭頭是道。他特別喜愛嘉義的魚翅肉羹與東港的蜂巢蝦仁。對於吃,唐魯孫兼容並蓄,而不獨沽一味。其實要吃,不僅要有好肚量,更要有遼闊的胸襟,不應有本土外來之殊,一視同仁。
唐魯孫寫中國飲食,雖然是饞人說饞,但饞人說饞有時也說出道理來。他說中國幅員廣寬,山川險阻,風土、人物、口味、氣候,有極大的不同,因各地供應飲膳材料不同,也有很大差異,形成不同區域都有自己獨特的口味,所謂南甜、北鹹、東辣、西酸,雖不盡然,但大致不離譜。他說中國菜的分類約可分為三大派系,就是山東、江蘇、廣東。按河流來說則是黃河、長江、珠江三大流域的菜系,這種中國菜的分類方法,基本上和我相似。我講中國歷史的發展與流變,即一城、一河、兩江。一城是長城,一河是黃河,兩江是長江與珠江。中國的歷史自上古與中古,近世與近代,漸漸由北向南過渡,中國飲食的發展與流變也寓其中。
唐魯孫寫饞人說饞,但最初其中還有載不動的鄉愁,但這種鄉愁經時間的沖刷,漸漸淡去。已把他鄉當故鄉,再沒有南北之分,本土與外來之別了。不過,他下筆卻非常謹慎。他說:「自重操筆墨生涯,自己規定一個原則,就是只談飲食遊樂,不及其他。以宦海浮沉了半個世紀,如果臧否時事人物惹些不必要的嚕囌,豈不自找麻煩。」常言道:大隱隱於朝,小隱隱於市。唐魯孫卻隱於飲食之中,隨世間屈伸,雖然他自比饞人,卻是個樂天知命而又自足的人。
一九九九歲末寫於臺北糊塗齋
序 陳紀瀅
近年來在報章雜誌讀到唐魯孫先生的許多文章。其中涉及範圍極廣,如北平飯館的各種特色,北平各階層的風俗習慣,城內外各種名勝,以及明清兩代的典章文物,無不說得頭頭是道,令人嚮往不止。我不多時就懷疑他必是北方賢者,而記憶力如此之強熾,觀察如此之細密,可以說寫同類文章的朋友,誰也比不了他。不但此也,他對江南文物,尤其飲食之道,所發議論,迥非南方朋友能如他那樣認真而詳細。在我未晤教以前,早已料到他是北平人無疑,是美食專家可信,是歷史學者無誤,而其記憶力之強,舉今世同文無出其右,他涉獵之多,更非一般人可比,他足跡之廣,也非寫遊記的朋友們可望其項背。但為什麼前幾年不見他的大作呢?這是我唯一存疑的一個問題。
約在三年前見面了,原來他服務公家,在服務之期事務太忙,無暇為文,且素性含蓄,藏而不露,不像我們知道一點兒便抖落出來,所謂一瓶不滿,半瓶晃蕩是也。他退休後,原住屏東,所以才乘退休之餘暇,慢慢的才把腹笥的貨色曝晒出來。遷來臺北後,著作更多。這種涵養功夫,足為後世法。魯公不但是北平人,而且是旗人,是旗人中的「奇人」,因為不是所有滿族都能對祖宗的事物深道其詳,不是所有北平人都會講食譜與說國劇,因環境不同、生活有異,所謂人各有愛好,見仁見智是也。
魯公所發表的文字,除非我看不見,只要看得見,我無不細讀細嚼,甚而一讀再讀,這在工業社會幾乎是不可能的,因時間不夠,能一讀再讀的文章,是多麼有吸引力啊!
我讀了魯公文章之後,打破了我許多自信:
(一)我是新聞記者出身,平素深以為自己留心事物不少,但看了魯公文章,則顯出自己粗心大意,漫不成章。以北平的名勝、膳食而言,自忖在北平前後六年之久,當窮學生時代,無錢看戲吃館子,但勝利後服務郵匯局,環境較好,每日應酬不暇,吃過了大小館子,理應對飲食一道知道較多,誰承望只顧吃了,卻忽略了肴饌之合成,更未深究其特色。當時僅知道誰家的館子賣什麼,什麼好吃而已。對於名勝亦然,每週無不去市郊遊覽,但對每一名勝只了解其大概,關於歷史沿革也只稍有模糊記憶,絕少考證,更沒有如魯公這樣把來龍去脈說得詳詳細細,而若干記載直如如數家珍。可知我這個「票友記者」(在《大公報》服務十五年,完全是客卿性質,並非「職業報人」,幸虧如此,否則早已陷身大陸)粗枝大葉,缺乏深入的了解,實有虧記者天職。
(二)我自四歲時起即有記憶力,數十年來,大小事情多數僅憑記憶,能道其顛末。近十五年來才開始寫日記,以幫助日漸衰退的記憶,讀了魯公的文章,才顯出比我記憶力強的至少有他一人。我的自負完全為之瓦解。
(三)我也自忖對世間之物有廣泛興趣。凡不屬我知識範圍的事物、學問以及許多雜事,大如天文、地理;小如引車賣漿之輩的生活,我都注意,但我還沒有如魯公注意範圍之廣,觀察之深。曹雪芹曾言:「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魯公辦到了,我還差得很遠呢!
當然魯公的文章給了我許多啟示,僅舉此三端,也夠我下一輩子學習的了。今欣知魯公與我同年,僅大我兩個月,但其學問,則何止高我二十年?
至於本書除趣味、歷史、民俗等等方面的價值而外,最重要的是可導引起中年以上人的無窮回憶與增加青年人的無限知識。凡無歷史感者,生於今世,不但有愧於做學問,甚至於可以說缺乏人生興趣。一個缺少人生興趣的人,還活得有什麼意思?
民國六十九年八月十八日一個酷暑的下午在大湖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