夢餘說夢 II
| 作者 | 黃愛玲 |
|---|---|
| 出版社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
| 商品描述 | 夢餘說夢 II:這兩卷本《夢餘說夢》,是作者黃愛玲最近十年的電影隨筆。作者的觀影隨筆,獨具一格。自幼愛看電影,作者說可能是跟她貪睡多夢有關。坐在黑漆漆的電影院裡,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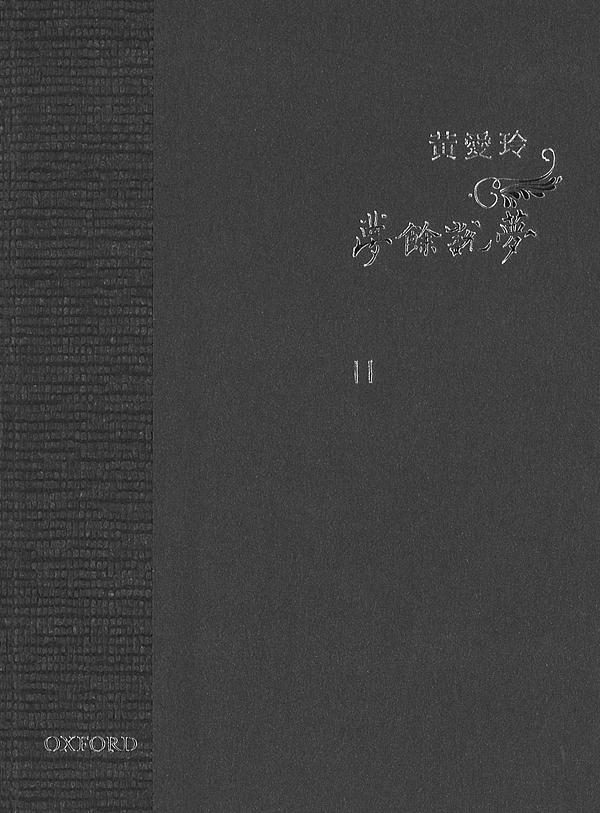
| 作者 | 黃愛玲 |
|---|---|
| 出版社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
| 商品描述 | 夢餘說夢 II:這兩卷本《夢餘說夢》,是作者黃愛玲最近十年的電影隨筆。作者的觀影隨筆,獨具一格。自幼愛看電影,作者說可能是跟她貪睡多夢有關。坐在黑漆漆的電影院裡, |
內容簡介 這兩卷本《夢餘說夢》,是作者黃愛玲最近十年的電影隨筆。作者的觀影隨筆,獨具一格。自幼愛看電影,作者說可能是跟她貪睡多夢有關。坐在黑漆漆的電影院裡,眼睛瞪著,精神卻是朦朧狀態,一任銀幕上的光影牽引,走進那太虛幻境。當然,也不是沒有清醒的時候,可看電影就如做夢,美也好惡也好,身體都不由自主地黏在座椅上,直到銀幕上打出一個「完」字,才遊魂似的重返意識的國度裡去。書名典出《聶紺弩舊體詩全編》,聶紺弩舊體詩好幾首都用上了「夢中說夢」四個字,其中「驢背尋驢尋到死,夢中說夢說成灰」特別悲涼,作者覺得貼心,改個字,變成了現在的書名。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黃愛玲黃愛玲 於1970-80年代遊學法國,返回香港後曾擔任香港藝術中心電影部負責人、香港國際電影節節目策劃、香港電影資料館研究主任。2000年出版影評集《戲緣》。
產品目錄 1 溫情滿人間4 中國電影的淒風苦雨8 蘇州河上的故事11 上海傳奇14 瘋狂的中國人17 花花世界真好21 沉沉的綠24 大山大水小故事30 山西風景34 楊德昌電影的家族譜37 侯孝賢的光影二夢51 夢裏不知身是客56 「敬你一杯酒,我的紅氣球」64 這個夏天真熱69 電影與人生72 無情的花樣年華75 天下無雙的愛情童話78 天女散花81 關錦鵬的私語86 明月千里寄相思90 春歸人面 相看無言93 廢墟裏的春天97 關在屋子裏的人102 寂寞的心106 朱石麟的夫妻篇——乍看三、四十年代遺珠幾顆113 《清宮秘史》二三事117 生死恨121 追求電影美學124 試探的藝術128 歷史的滄桑139 紅樓夢未醒143 中國電影史上的黑洞149 憂傷與憐憫154 不倒的女性162 天真的虛榮166 毀 滅174 漆黑裏的笑聲177 人人看我 我看人人180 大宅後的玫瑰園184 六十年代的青春物語187 ??轉 菊花圓191 現代萬歲——光藝的都市風華195 拼拼貼貼說電懋204 浮桴託餘生209 歸宿這小島上——淺談岳楓213 時代的標誌——張徹與易文218 香港故事221 電影之死225 夢遊威尼斯229 編後語231 索 引
| 書名 / | 夢餘說夢 II |
|---|---|
| 作者 / | 黃愛玲 |
| 簡介 / | 夢餘說夢 II:這兩卷本《夢餘說夢》,是作者黃愛玲最近十年的電影隨筆。作者的觀影隨筆,獨具一格。自幼愛看電影,作者說可能是跟她貪睡多夢有關。坐在黑漆漆的電影院裡, |
| 出版社 /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
| ISBN13 / | 9780193978805 |
| ISBN10 / | 0193978806 |
| EAN / | 9780193978805 |
| 誠品26碼 / | 2680675836005 |
| 頁數 / | 268 |
| 開數 / | 32K |
| 注音版 / | 否 |
| 裝訂 / | H:精裝 |
| 語言 / | 1:中文 繁體 |
| 級別 / | N:無 |
內文 : 溫情滿人間
看張藝謀的近作《一個也不能少》(1999) 和《我的父親母親》(1999),令我一而再地想起基阿魯斯達米 (Abbas Kiarostami) 電影裏那條永恆地蜿蜒曲折的山路,有時候也會反躬自問,是否對他有點不公平。難道基阿魯斯達米買下了拍攝山路的專利權不成?在電影的世界裏,「路」向來引發人們無限的聯想,從孫瑜的《大路》(1934) 到費里尼 (Federico Fellini) 的《大路》(La Strada, 1954),它可以引領我們走向光明美好的未來,也可以只是人生殘酷無情的過程,內裏蘊藏了無盡的玄機。說句老套話,路是人走出來的,有人就有路,有路就有人的故事,西方公路電影的傳統由來已久,現在連中國也開始拍出帶點公路電影味道的《非常夏日》(路學長導演,1999)來了。
當然,除了沿海地帶,中國還是貧窮落後的居多,第五代以來,不少中國電影展現了這些並不討好的人文景觀,有些也因而被譏為討好外國口味。曾幾何時,張藝謀也受過類同的批評,今天他卻彷彿成為了中國主流電影的代言人。打從他的處女作《紅高粱》(1988) 開始,張藝謀已深明電影作為大眾娛樂的特質,注重?事的技巧,總能將故事說得娓娓動聽,比起同輩導演的作品來,他的電影也就顯得「好看」。猶記得八七年在北京看到剛完成初剪的《紅高粱》,片中的感情流露有一股張揚跋扈之氣,令人興奮暢快,那舒展的感覺要待得九十年代看姜文的《陽光燦爛的日子》(1998) 時才重現。那個時候的張藝謀對性顯然並不忌諱,高粱地裏野合一場,便有一份中國電影裏少見的理直氣壯。相反地,兩年後的《菊豆》(1990) 便壓抑得令人透不過氣來。假若《紅高粱》是一個中國人嚮往已久的神話—— 做人合該如此酣放,《菊豆》便是中國人現實裏精神面貌某種寓言式的呈現——人性扭曲變態,連男女交歡也要偷偷摸摸、猥猥瑣瑣。 兜兜轉轉,張藝謀的《我的父親母親》又回到了他投身電影之始的愛情題材,作品背景不再是含糊的「從前」,而是以一個九十年代壯年人的眼光,回憶父母在五十年代反右時期一段刻骨銘心的愛情故事。在片中,反右這個歷史背景並不重要;它充其量像一層薄紗,讓背後搬演的故事添上一抹朦朧的童話色彩。在片中,現實是黑白而回憶才是色彩斑斕的。然而,相對於張藝謀電影裏八十年代「阿爺」的神話或九十年代的人性悲劇,這則總結二十世紀的愛情童話便顯得貧弱乏力。基阿魯斯達米的《風再起時》以一則事先張揚的死亡來反思生命和電影,張藝謀卻以一場古老的喪葬儀式為歷史劃上句號,不再反思,輕飄飄的像根羽毛。英文片名是The Way Home,似乎比中文原名更能點題——可以回家就是好了。
近年來,中國電影溫情處處,周友朝的《一顆樹》(1996) 和《背?爸爸上學去》(1997)、霍建起的《那山那 人那狗》(1999) 等,都寫中國人民的堅毅有情——環境縱然惡劣,我們總能熬得過去,只是??問題嘛,還是免問的好,而張藝謀顯然比任何人都更清楚、更有技巧。
2000年12月22日
中國電影的淒風苦雨.
拿起一份「中國經典電影回顧展」的宣傳單張,心裏有說不出的滋味。你可以想像曾拍過婉約清麗的《早春二月》(1963) 的謝鐵驪,七年後導演了「革命樣板戲」《智取威虎山》(1970) 嗎?記得一位國內友人曾說,有時候無緣無故哼起歌來,從喉嚨裏吐出來的竟是《智取威虎山》裏偵察排長楊子榮的詞兒,連他自己也會大吃一驚;回頭想想,他那青?的歲月就是那麼樣在楊排長高吭的嗓子裏磨蝕掉的。說的輕輕鬆鬆,聽的倒有幾分惆悵。自從打倒「四人幫」以來,革命樣板戲便消聲匿跡,民間看了十年的樣板戲不想再看是自然不過的,但官方意圖將這段歷史從人們的集體記憶中不動聲色地抹掉,卻令人極度不安。這次回顧展能讓它重現人們眼前,從歷史的角度看絕對是一件好事,黑的白的灰的,人們應該有足夠的能力自己來作判斷,但以它作為開幕電影,卻總有一點 celebrate 的意味,令人看?不能不有點怪怪的。
電影常常是現實生活最貼切的注腳。在《早春二月》裏飾演可憐寡婦文嫂的,就是文革初期跳樓身亡的上官雲珠。在影片中,她也抵受不了生活的壓力而自殺,一如她在另一部同年代作品《舞台姐妹》(1965) 裏的悲苦命運。上官雲珠的女兒韋然在〈何以告慰一個屈死的靈魂?〉一文中,曾有以下數行令人滄然淚下的文字:「媽媽從樓上跳下,落在菜市場準備上市的菜筐裏,當時還可以向圍上來的人們說出家裏的門牌號碼??」。那是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的凌晨,我幾乎聽到了那日常生活的悉悉蟀蟀聲。
《早春二月》的故事發生在二十年代中浙東一個叫芙蓉鎮的地方,謝晉拍於一九八六年的《芙蓉鎮》,說的可是同一個地方?鏡頭所及,嫵媚醉人的江南景色變成了灰頭土腦的蕭索淒涼。在偉大的紅太陽底下,眾芳萎絕,片中的劉曉慶與姜文卻有若那風雨蘭,在淒風苦雨中猶自綻放,不卑不亢。八十年代,從文學到電影,無不「傷痕」纍纍,謝晉卻成功地將之轉化為催人淚下的戲劇,一代人在漆黑的戲院裏盡情宣洩,以淚水洗滌傷口,然後走出影院,抖擻精神,迎戰無堅不摧的經濟大浪潮。水華導演、夏衍改編自茅盾小說的《林家舖子》(1959) 拍的就是經濟大環境對普通小市民生活的影響,不過年代是大半個世紀前的一九三一,地方卻也是江南水鄉。
水華固然是一九四九年後中國電影的一名大將,夏衍的經歷卻更能說明作為一個中國文化人的複雜與悲哀。近讀丁亞平的《老電影時代》(大象出版社,2002),其中討論夏衍的一章引述了沈芸的一段話:「有一種相當普遍的看法,認為夏衍在一九四九年前是文化人,之後則是文藝的領導人??[他] 一方面要執行黨制定的方針政策,另一方面在黨內又不斷挨整,擺脫不了當時的身份和尷尬處境。」丁亞平亦提及夏衍於新中國成立之初,曾因向崑崙和文華兩間民營公司推薦了《關連長》(1951) 和《我們夫婦之間》(1951) 兩個劇本而承受過不少壓力,也成了後來全國性批判《武訓傳》(1950) 的前奏。因此,當他主管電影後,便採取了比較保險的辦法,只改編魯迅、茅盾等官方認許的作家的作品,但即使謹慎若此,仍逃不了挨批的命運,《林家舖子》於一九六五年被「圍剿」,文革時夏衍更和無數同代人一 樣,進了秦城。
至於第五代那一輩的電影,這次回顧展選了陳凱歌的《黃土地》(1984) 和張藝謀的《紅高粱》(1987),不是 質疑它們的「經典」地位,只可說這選擇是太謹慎了。是否也可找張軍釗的《一個和八個》(1984)、田壯壯的 《獵場扎撒》(1985) 和《盜馬賊》(1986)、胡玫的《女兒樓》(1985) 等來放映?比起《黃土地》和《紅高粱》, 它們太少曝光的機會,大可藉此重新審視那段歷史。就拿《一個和八個》來說,它完成的時間比《黃土地》早,藝術野心也絕不比後者小,但際遇卻差多了。搞電影節目,重要的是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