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ties and Cinema
| 作者 | Barbara Mennel |
|---|---|
| 出版社 | 群學出版有限公司 |
| 商品描述 | 城市與電影:城市電影,為那些認得自己的城市,以及城市對他們而言宛如遙遠夢想或夢魘的人,製造了幻想。電影重塑城市規劃者的希望,卻再造了城市居民對於現代都市的恐懼。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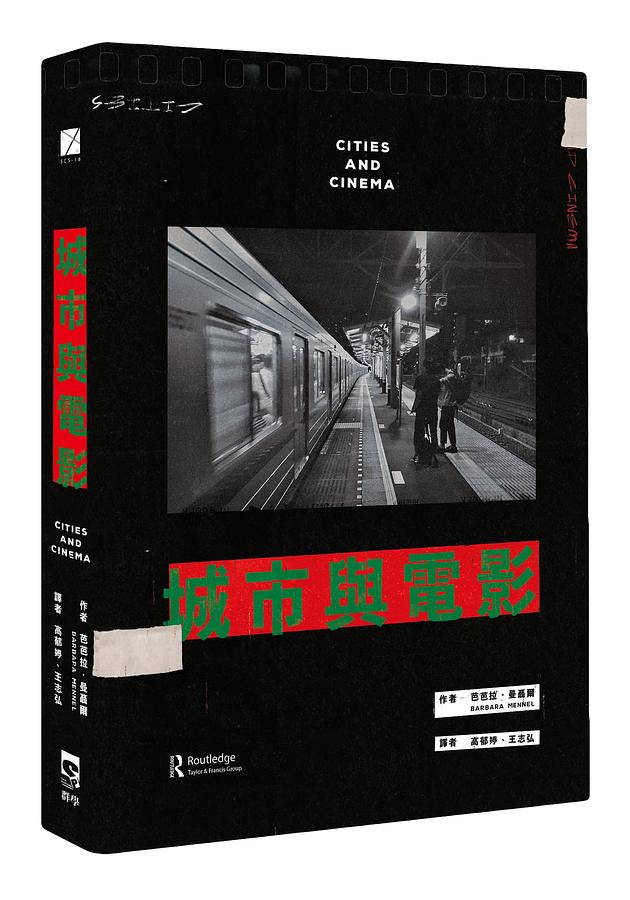
| 作者 | Barbara Mennel |
|---|---|
| 出版社 | 群學出版有限公司 |
| 商品描述 | 城市與電影:城市電影,為那些認得自己的城市,以及城市對他們而言宛如遙遠夢想或夢魘的人,製造了幻想。電影重塑城市規劃者的希望,卻再造了城市居民對於現代都市的恐懼。 |
內容簡介 城市電影,為那些認得自己的城市,以及城市對他們而言宛如遙遠夢想或夢魘的人,製造了幻想。電影重塑城市規劃者的希望,卻再造了城市居民對於現代都市的恐懼。分析城市電影可以回答都市研究的叩問嗎?城市電影提供了什麼樣的未來願景及過去意象?城市電影經歷了什麼變化? 《城市與電影》召喚都市理論和電影研究對話。第一篇依照歷史順序,分析三種重要的城市電影類型,每一種類型都與特定城市有關:威瑪共和的城市電影、洛杉磯的黑色電影,以及法國新浪潮(French New Wave)電影的巴黎意象。第二篇討論了都市研究的社會-歷史主題。首先是電影產業和個別城市的關係,接著是描繪飽受戰爭荼毒及分隔的城市,最後是都市科幻小說中,烏托邦和惡托邦的電影表現。最後一篇則是在全球化世界中,協商認同與地方的問題:從貧民窟與族裔聚居區,轉移到男女同性戀慾望的城市場景,最後以跨國電影實踐裡的全球城市再現作結。城市和電影之間的連結是現代性。現代性解釋了城市電影通過全球化過程而產生的大變遷,在這個過程中,城市從國族電影的象徵,發展成為跨國電影實踐的優勢位址。本書允為電影研究、都市研究及文化研究學生與研究者的關鍵讀本。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芭芭拉.曼聶爾(Barbara Mennel)任職位於蓋恩斯維爾(Gainesville)的佛羅里達大學,擔任日耳曼與斯拉夫研究系,以及英語系電影與媒體研究學程的德國研究暨電影研究助理教授,撰有《電影與文學之受虐狂與酷兒慾望再現》(The Representation of Masochism and Queer Desire in Film and Literature, 2007)。■譯者簡介高郁婷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生。王志弘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
產品目錄 圖目錄謝誌導論:電影創世神話或「火車效應」第一篇1 現代性與城市電影:柏林2 黑暗城市與黑色電影:洛杉磯3 愛之城:巴黎第二篇4 城市電影產業:香港5 廢墟之城與分隔之城:柏林、貝爾法斯特與貝魯特6 烏托邦和惡托邦:夢幻與虛擬之城第三篇7 族裔聚居區與西語區8 城市是酷兒遊樂場9 全球城市與全球化中的城市結論:從「火車效應」到「貧民區效應」-如何做更多研究註釋參考書目片單索引
| 書名 / | 城市與電影 |
|---|---|
| 作者 / | Barbara Mennel |
| 簡介 / | 城市與電影:城市電影,為那些認得自己的城市,以及城市對他們而言宛如遙遠夢想或夢魘的人,製造了幻想。電影重塑城市規劃者的希望,卻再造了城市居民對於現代都市的恐懼。 |
| 出版社 / | 群學出版有限公司 |
| ISBN13 / | 9789869470896 |
| ISBN10 / | 9869470890 |
| EAN / | 9789869470896 |
| 誠品26碼 / | 2681727816006 |
| 頁數 / | 384 |
| 開數 / | 25K |
| 注音版 / | 否 |
| 裝訂 / | P:平裝 |
| 語言 / | 1:中文 繁體 |
| 級別 / | N:無 |
內文 : 導論:電影創世神話或「火車效應」
電影統治著城市,宰制了大地……它比智者的講道有力,向所有人展現了何謂現實(Andrei Bely, 1908)。
電影傳誦不止的創世神話,正位於巴黎:
「1895年12月28日,電影起源於巴黎凱普辛大道(Boulevard des Capucines)上,大咖啡館(Grand Café)的地下室,」薇姬.樂博(Vicky Lebeau)說道(1)。她說的當然是盧米埃(Lumière)兄弟「電影」(Cinématographe)那神話般的首度公開登場,他們將運動影像投射到銀幕上,令觀眾目眩神迷。巴黎城也是這段電影創建故事中,不可或缺的一角。樂博記述道,當時記者將這樣的經驗描述成「瀕臨恐懼的興奮」,而在某些時刻,她認為「恐懼變成了驚慌」(1)。樂博說,盧米埃兄弟放映僅50秒長的默片短篇《火車進站》(The Arrival of a Train at La Ciotat station, 1895)時,驚慌尤為鮮明,這部電影「應該要讓觀眾驚恐起身、遠離銀幕,對臣服於影像幻覺的觀眾來說,與直衝而來的龐然機器相撞的驚懼,實在是太強烈了。」這個將現代性元素——都市性、速度、電影與城市——融於一爐的開創性時刻,這個傳誦不已的神話,其實重製了電影講述的自身故事:當燈光熄滅,錯覺變得近乎真實,我們忘了正在觀賞的不過是動畫而已。
尤里.茨維安(Yuri Tsivian)將早期觀眾對銀幕上逼近的火車感到驚慌的反應,稱作「火車效應」(train effect)(Bottomore 178)。但已經有學者證明,描述全體觀眾都為了看似逼近的火車而驚恐萬分,其實誇大了少數人才會有的反應(參見Bottomore; Christie; Clarke and Doel)。在卡通、文學,甚至是電影自身中,都能看到動畫火車的再現與真實成為發揮的主題,這在世紀轉折之際,早已屢見不鮮。尼古拉斯.西雷(Nicholas Hiley)相信,驚慌的電影觀眾的這種想法,在1920至1930年代萌發,而當時這類故事已在民間流傳了二十年(Bottomore 184)。這些敘事上的修正,說明了後來的觀眾對於電影作為一種新媒介,其實擁有純熟的解讀能力。
史蒂芬.巴特摩(Stephen Bottomore)在研究早期的電影節目單後,認為描述火車旅程的短片比起其他同時期短片更令人感到壯觀,他也宣稱早期電影在放映結束時,會造成「一種感官顫動」(a kind of sensation)(179)。戲院主人會利用、甚至煽動極端的身體與情緒反應。例如:紐約的東尼帕斯特(Tony Pastor’s)戲院在放映詹姆士.懷特(James H. White)搭配火車音效的一分鐘《黑鑽石快遞》(The Black Diamond Express, 1896)時,找來一輛救護車待命。會這麼安排,是因為兩名女性觀眾曾經在稍早的放映裡「尖叫昏厥」,但後來發覺她們只是「差點昏過去」(Bottomore 181)。顯然,當時的觀眾還必須學習如何在認知上與新媒體協商,找到信以為真和不予置信之間的平衡點;這也正是看電影時,能否獲得快感的前提。許多流傳於印刷媒體中,有關驚慌恐懼的指涉,無論是來自正經文章還是廣告,也顯示了廣告行銷正要開展,而廣告仰賴著羶色腥刺激。據此,學者也開始挖掘電影的創世神話,找尋它所述說的現代性,這包括時間與空間感知的轉變,以及創造出一批被編碼為屬於城市且世故熟練的現代觀眾。1895年,當那場名氣響亮的放映在大咖啡館啟動之際,電影的歷史其實早已上路了。
……
城市裡的早期電影,與早期電影裡的城市
與電影的創世神話相反,電影於世紀之交發展時,巴黎並非唯一重要的城市。藝術和科技方面的交流,也發生在倫敦、柏林、莫斯科和紐約,它們都是滋養早期電影發展的地方。於是,電影的成長與城市的成長緊密連結,而城市也和電影院這種都市娛樂消遣場所的發展有關。電影在音樂廳及雜耍(vaudeville)劇院裡,跟現場表演一起交替演出,甚至在固定電影院出現以前,還有稱作「窺視秀」(peep-shows)的「巡迴電影演出」(Christie 51)。但是,製作電影的資本還是要從城市裡尋找,而且將電影院建在城市裡,才能賺取更多利潤,因為都市人口的可花用收入和餘暇正不斷增加。
電影影響了城市的門面和形貌。所謂的拱廊街「遊樂廳」(parlours)就是一個經常供電影放映的場地。裡面有「窺視秀機器」(peep-show machines),專供個人觀賞,提供不同於集體觀看投影式電影的經驗(Christie 51)。大概從1905年開始,投影的電影觀看方式,才使專為電影放映設計的建築物成為必要。它們被稱作「五分錢戲院」(Nickelodeons),席位不滿兩百,以避免課徵劇院稅,客群則鎖定中下階級和移民(Christie 51)。幾年後,電影界開始改變電影內容,建造豪華戲院以迎合中產階級觀眾。在巴黎、莫斯科和柏林,這些有管弦樂團、奢華內裝與外觀的戲院,成為都市有閒階級的新興現代娛樂殿堂。正如我們在第一章即將看到的柏林例子,這些電影殿堂成為1910與1920年代,社會學與哲學論辯的主題。
即使巴黎不是唯一與早期電影發展有關的城市,但它不論在實際或象徵意義上都是重要場所。在奧斯曼男爵(Baron Georges-Eugène Haussmann)主導的再概念化與再發展底下,巴黎的都市改造令它成為現代性的象徵標誌。奧斯曼著名的作為,便是在十九世紀中期,將巴黎從原本有機成長的城鎮型態,改造成經過規劃的大都會。這個嶄新的巴黎考慮了現代科技,像是鐵路和煤氣燈,令交通在通往火車站的大道上川流。建築物與一條條筆直的規劃街道,呈現前所未見的統一性質。奧斯曼擘畫並執行的城市景觀,成為直至今日的巴黎特色,其中也包括那個現代性符徵——艾菲爾鐵塔(the Eiffel Tower),它代表了這個卓越的世界城市。甚至連1950年代早期至1960年代初期的法國新浪潮電影,也用奧斯曼的城市景觀來捕捉道地的巴黎都市經驗。
奧斯曼創造了一個垂直組織的城市,排水系統的地下世界與稍晚的地鐵,都具體呈現了一種隱蔽的現代性,進入了與城市有關的電影裡。不僅是以巴黎為場景的電影,這種垂直組織在其他未將場景設定在巴黎的電影中,也承擔了象徵和隱喻上的深遠意味,就如同我們在弗里茨·朗恩(Fritz Lang)的《大都會》(Metropolis, 1927)、卡洛.李德(Carol Reed)的《黑獄亡魂》(The Third Man, 1949)和李察.唐納(Richard Donner)的《超人》(Superman, 1978)中將看到的,它們把意識形態的價值觀和階級結構,映繪到上層與下層世界的都市結構中。
一、現代性與城市電影:柏林
今日,所有階級都湧向了電影,下至市郊電影院的工人,上至豪華劇院的上流布爾喬亞。(Siegfried Kracauer)
現代主義美學:城市交響曲
街道電影提供由角色演繹的通俗敘事,其他電影如魯特曼(Ruttmann)的《柏林:城市交響曲》(Berlin: Symphony of a Great City),則在不仰賴傳統敘事的情況下,再製了現代性的心理和視覺經驗。黑可(Hake)就認為《柏林:城市交響曲》是激進的,原因是它「從視覺角度」組織了柏林的「社會與空間性質」(1994: 127)。然而,儘管這部電影的前衛與現代主義美學表現受到許多讚揚,黑可卻認為魯特曼的「最終目標是視覺愉悅,並非批判分析」(1994: 127)。
在魯特曼的電影裡,通過一整天的時間組織安排,將柏林這個現代都會予以擬人化;自始至終,魯特曼安排了五幕場景。開場鏡頭是沈靜的水波與陽光,映射出抽象形狀:一個圓圈、幾條線、和一個方形以抽象的構型移動,伴隨短促不成調的配樂。抽象開場後接著切入的鏡頭,則來自往柏林移動的火車,它穿越周遭的農園、工業區、營建工地、空蕩的火車站,以及各種廣告,最後是預告抵達柏林的標誌。下一個序列以近拍的機械,象徵現代化生產的匿名性和效率,並和自上方取鏡的柏林大教堂展現的舊時榮光呈現對比。大都會中的人類,在現代主義建築、工業設計和電力設備的鏡頭裡,一直都是現代性物質面的從屬者。第一幕中,早晨五點空蕩的街道,強調的既是人的缺席,也是城市本身作為實體的缺席,成為這部電影此處的獨特焦點。
電影中,先是有不同形狀剪輯構成的抽象開場,形成富有節奏的圖案,接著是駛進城市的火車。這樣的序列編排並非僅是考量形式,還反映了凱斯(Kaes)所說的一項事實,「柏林一直都是鄉村移居者的城市」(1998: 185)。電影開頭將自然與抽象形式置於兩極,框構出現代主義大都會的概念。黑可形容這樣的剪輯模式是「一種聯想式蒙太奇(associative montage)」,和謝爾蓋.愛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一派的政治評論不同,聯想式蒙太奇「確認了全然的可交換性和永恆的重覆性,是現代大眾文化經驗的基礎」(1994: 130)。她還指出,電影並未凸顯十九世紀時能辨認出帝國柏林的紀念碑,這與先前的城市理解相比,是一大轉變(1994: 134)。攝影機不斷重複城市中某些地方的鏡頭,藉此來標誌出現代都會,這些地方受到指認,不是因為在德國首都具有國家重要性,而是因其扮演的交通或休閒角色。我們在電影中看見的不是建築,而是交通,延續了對移動的著迷,並且以剪輯的動態可能性展現出交通的動態可能性。魯特曼是一位受過訓練的畫家,史錐德森( Strathausen)解釋道,魯特曼在電影放映前曾發表聲明,說自己的蒙太奇技法達成了「音樂與節奏的要求」(43)。
《柏林:城市交響曲》反覆呈現商店櫥窗中的時裝模特兒,將它們人造而擬人的特性,與商品的誘人魅力結合起來。時裝模特兒受到精心擺設,激發視覺的愉悅感,引誘潛在的漫遊者進入店內購物。這樣的景象與路上的人潮並置呈現,他們可能在上班的路上、或是抵達崗位正要開工,他們快速地在地鐵樓梯上下穿梭,呈現了斷裂感。鏡頭是根據移動和構圖的抽象原則組成,上班的人群與列隊行進的士兵及動物的鏡頭交錯剪接,鏡頭持續切換,人潮數量也隨之增加。在城市中移動的人潮景象,進一步與凸顯人類渺小的工業、機械及電力機器的近景拍攝交錯;我們還看見象徵現代性的傳播工具,像是打字機和電話。
最佳賣點 : 城市和電影之間的連結是現代性。現代性解釋了城市電影通過全球化過程而產生的大變遷,在這個過程中,城市從國族電影的象徵,發展成為跨國電影實踐的優勢位址。本書允為電影研究、都市研究及文化研究學生與研究者的關鍵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