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chnology and Social Theory
| 作者 | Steve Matthewman |
|---|---|
| 出版社 | 群學出版有限公司 |
| 商品描述 | 技術與社會理論:,STS×社會理論,迸出哪些新滋味?眾多技術物案例,捕捉社會與「非人類」的交引纏繞人類世時代必讀的科際研究入門書「人性始於物。」──賽荷(MichelSerr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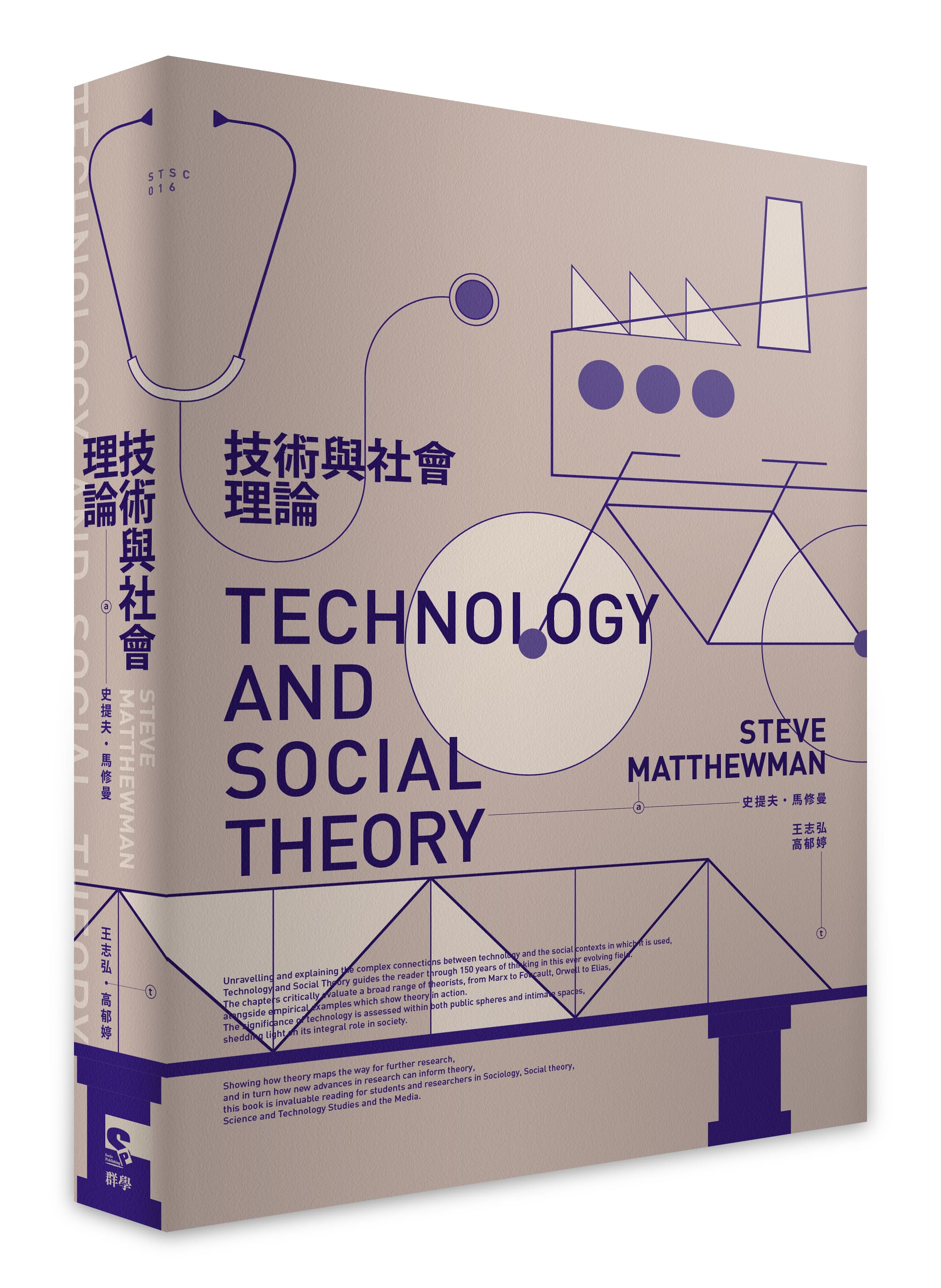
| 作者 | Steve Matthewman |
|---|---|
| 出版社 | 群學出版有限公司 |
| 商品描述 | 技術與社會理論:,STS×社會理論,迸出哪些新滋味?眾多技術物案例,捕捉社會與「非人類」的交引纏繞人類世時代必讀的科際研究入門書「人性始於物。」──賽荷(MichelSerr |
內容簡介 STS×社會理論,迸出哪些新滋味? 眾多技術物案例,捕捉社會與「非人類」的交引纏繞 人類世時代必讀的科際研究入門書 「人性始於物。」──賽荷(Michel Serres) 「若是物質性、人造的世界不存在……我們這些解剖學意義的現代人類,幾乎不可能慮及社會。」──拉圖(Bruno Latour) 何謂技術?技術與社會的關係是什麼?是新技術的出現,無情地推動社會變革,抑或,技術僅僅是社會的工具,受到人類意圖的擺佈,正所謂: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 上述兩種想法分別反映出技術決定論及社會決定論的觀點。前者對科技抱持「反人文主義」(anti-humanism)的立場,認為技術具有絕對的自主性,位於社會關係之外,技術帶給文化的後果則是線性的,像是「網路必能摧毀極權政府」之宣稱即屬於此觀點。反之,「人文主義」(humanism)則強調技術無非是社會的建構,儘管這點正確,然而此類推論一旦走向極端,物質性的現實將遭到忽略,彷彿自然或人造物本身的性質,在社會變遷中所扮演的角色微乎其微。 近期,在科學與技術研究(STS)的領域,逐漸浮現出一種更能兼顧物-社會複雜性的取徑,也就是「後人類主義」(post-humanism)。後人類主義不只認為技術具有能動性,還認為人或社會本身就是一種各種異質存在物交錯形成的網絡。這個觀點把技術與社會視為交互纏繞,而非互斥二分。從所有權、控制權、近用權、使用方式及非意圖後果這五大面向出發,有助於我們全方位分析技術物的效應,而非落入決定論的陷阱。 最後,本書具有豐富的實例,從橋樑、錄影帶、腳踏車到3C產品,這些人造物的發展史往往超乎大家想像;再者,相較於坊間的STS文本,本書更涉入了社會理論的領域,探討馬克思、涂爾幹、班雅明、阿多諾、傅柯、麥克魯漢、拉圖等人如何構思技術與物。在這個科技變革日新月異的時代,與公民權益切身相關的「技術與社會」議題早已成為顯學,而此書則期盼能提供讀者實用的概念工具。 佳句摘錄 ☆論技術與社會 解蔽(revealing)是技術的本質。據此,技術是一種認識的形式,其重要性是形上學式的,但此處的形上學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意義:否認真理即是揭露,以及,認為每次揭露也都伴隨著隱蔽(Heidegger, 1969)。令現代技術獨特的是它們牽涉的特殊解蔽形態。一切技術皆嘗試去挑戰自然,去解鎖、轉化和貯藏其能量。 技術是社會焦慮的主要來源:(1)現代技術是延展且開放紋理的,即使是專家也苦於掌握它們;(2)技術的意圖結果實際上可能無法實現;(3)技術是即時的實驗,具有報復作用,它們就是等著發生的意外。 對許多理論家,包括伍爾加(Woolgar, 1991, p. 46)而言,何謂技術,無法由設計來決定。相反,技術的意義總是要在使用中發現。他引述電話的例子,電話最初是設計作為大眾廣播技術,而非個人對個人的技術。 技術沒有本質,只有群體賦予它的意義。不同群體對於技術會有不同觀點;因此,技術具有詮釋彈性(interpretive flexibility)。最後,詮釋彈性會減少,許多種解讀會減少到一種。當技術達到了穩定化與封閉(closure)後,第二步就停止了。 如果一名單車騎士因為撞上石頭而摔車,社會科學家坦承,他們沒有什麼好說的……對STS(科學與技術研究)的實踐者而言,情況不是如此,他們認為單車本身的運轉機制、道路的鋪設、石頭的地質學、傷口的生理學等等,都在社會學上有意思,而且在經驗上可以分析,不需要將物質和社會之間的界線,當成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之間的分工(Latour, 2000, p. 108)。 我們唯有在技術沒有依照預期而運作的情形下,才會注意到技術。 ☆論現代 決定性的轉變源自馬克思所謂由主觀到客觀的技術變遷:工人曾經掌控工具,如今卻是機器掌控工人。 從中世紀延伸到1900年的時期,藝術的發展超過了技術的發展。突然間,局勢逆轉了。技術主宰了藝術的步調。 如果規訓是奠基於訓練,並且著眼於個人的身體之微政治技術,那麼生命權力(biopower)就是安全的宏觀政治技術,其目標是全體人口。 ☆論後人類主義 馬克思傾向於認為技術是(人類)力量的延伸,而麥克魯漢認為是感官的延伸,特克爾(Sherry Turkle)認為電腦是心靈的延伸。 技術總是徹底擬人的:它們由人類製造和使用,它們會做原本由人類做的事,而且它們會進一步塑造何謂人類。 我們所不是的東西投射進入了物品。物體拜物教經常用來當成推進的工具。在這裡,物成為我們社會地位的指標。 哈洛威(Donna Haraway)清除了流行的說法,也就是「狗有主人,貓有員工」。她主張狗也會訓練我們,而且牠們的馴化是一種共同生產,而不是只有人類的努力。 我們已經與我們的技術共同演化了幾百萬年……它們是身為人類的必要部分,或許是我們最富人性的元素(McLuhan, 2005, p. 289)。聲稱我們總是後人類,說的就是這回事。我們從來沒有先存於或獨立於技術、同伴物種和環境,它們協助建構了我們。我們的聚光燈需要照亮這些領域。 本書特色 ◆詳實回顧技術社會學的重大典範轉移,不只清楚呈現SCOT(技術的社會建構)、ANT(行動者網絡理論)等各大學派的主張,亦對學派之間的異同進行了比較。 ◆在照顧STS傳統的同時,也是非典型的STS讀物,將眾多社會理論的「技術」面向納入考慮,甚至有大量篇幅與傳播學、物質文化、空間研究等領域對話。 ◆案例豐富多元,涵蓋機器、媒介、器具、資訊、交通、養殖動物、寵物等,幾乎無所不包,而在分析維度上亦面面俱到,每章末尾也列出並解說進階讀物,有助於讀者更加深入探索各種理論或實例。 專業推薦 本書爬梳了社會學取向的勞動過程論與跨學科取向的STS研究之間的系譜。──David Calnitsky(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超越學科畛域,開創更貼近周遭、有學有術、兼容並蓄的技術社會論述。──郭文華(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教授)
作者介紹 史提夫.馬修曼(Steve Matthewman)紐西蘭奧克蘭大學(University of Auckland)社會系的社會學高級講師。他在社會學領域有擔任作者和教師的資深經驗,特別關注科學與技術、社會理論、文化研究,以及現代性及其不滿等議題。王志弘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高郁婷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博士後學者。
產品目錄 導讀 將技術寫入社會,將社會納入技術的理論複習/郭文華 叢書序言 致謝 導論 本書組織│社會理論的要旨│關鍵主題 第一章 技術的理論化 何謂技術?│技術做了什麼?│技術如何被理論化?│技術、系統與社會利益│我們的時代:技術、複雜性與風險 第二章 馬克思、現代性與機器 物質轉向│機器製造的機器:現代工業│機器製造的人群:現代主體性│馬克思與技術決定論│馬克思的延伸I:批判理論與文化工業│馬克思的延伸II:諾布爾,《生產的力量》 第三章 建構現代:人造的世界 城市中的社會理論│《拱廊街計畫》│班雅明論漫遊者與技術│傅柯作為技術思想家│技術之眼│工具變遷:技術創新│《規訓與懲罰》:技術問題的技術解答│傅柯與權力機制:技術的中介角色│傅柯2.0:理論與技術升級│忘了傅柯?│附論:創造秩序I-愛里亞斯與建築物的政治 第四章 人造物的政治 技術作為陰影構成│社會工程:摩西切割布朗克斯並建造橋梁│對溫納的批評│技術戲劇│附論:創造秩序II-空間的政治 第五章 技術的社會建構 社會學重新發現了技術│有爭議的技術│固定意義:單車的黑箱化│對SCOT的批評 第六章 社會的社會技術建構:行動者網絡理論 與社會建構論決裂│社會學:有什麼好處?│轉譯社會學│異議的能動者│傅柯/ANT│對ANT的批評 第七章 留給我們自己的設備:主體機器 覺察變遷│第二自我:個人電腦│隨身聽的異議:文化產物的傳記│連上你的自我:私人世界與iPod│從我們的空間到我的空間:公共生活的私人化 第八章 客體生活:物與社會理論 社會生活的物│物的社會生活I:技術生命週期│物的社會生活II:技術生命週期與存有論交換│物的綠化:永不停歇的螺旋│準客體:後人類主義與同伴物種 結論:我們從來都是後人類
| 書名 / | 技術與社會理論 |
|---|---|
| 作者 / | Steve Matthewman |
| 簡介 / | 技術與社會理論:,STS×社會理論,迸出哪些新滋味?眾多技術物案例,捕捉社會與「非人類」的交引纏繞人類世時代必讀的科際研究入門書「人性始於物。」──賽荷(MichelSerr |
| 出版社 / | 群學出版有限公司 |
| ISBN13 / | 9786269650125 |
| ISBN10 / | 6269650127 |
| EAN / | 9786269650125 |
| 誠品26碼 / | 2682336599007 |
| 頁數 / | 376 |
| 開數 / | 25K |
| 注音版 / | 否 |
| 裝訂 / | P:平裝 |
| 語言 / | 1:中文 繁體 |
| 尺寸 / | 14.8X21X2.2CM |
| 級別 / | N:無 |
導讀 : 將技術寫入社會,將社會納入技術的理論複習
郭文華(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教授)
寫此文時台灣選戰方酣,手法也推陳出新:有用影像估算造勢人流的,有用假帳號操弄社群聲量的,有巧剪影片段延伸演繹的,有設計民調操作外宣的。還記得當年首開先例,用廣播節目調動遊行人群,顛覆傳播媒體的爭議。曾幾何時,這些技術都已成為標準配備,經由「小編」、「網紅」,或者是「意見領袖」的加工,帶動民意的風向。
其實,選舉只是技術社會,或者說技術社會集合體(collective)的縮影。台灣自1990年代起幾乎年年選舉,而且兩黨鬥法的態勢混淆它們的差異與目的,變相成為民主嘉年華或試金石,刺激相關技術的演進──有打形象的空戰,有掃街拜票的陸戰,更有玩弄民調與媒體節奏的資訊戰。相較於此,攸關未來的改革,如健保資料庫的釋憲後續,人工智慧(AI)的公共化、或者下修公民權年齡等,有些得到青睞,迎合時勢,成為成就「台灣第一」論述的註腳,但大部分則欠缺討論溝通,也沒技術加持,一推出就埋在空洞的政策與選舉語言中。
這是我們需要《技術與社會理論》,審視技術社會相關理論工具的起點。作為科技與社會研究(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studies, STS)的實踐者,我不低估技術,認為它只是奇技淫巧或雕蟲小技,也不會掉進創新迷思,認為技術是社會進步的主要推手。甚至近來台灣學界常用,技術與社會互動共製的說法,在STS研究中也已是老生常談。
但相較於將解釋技術社會當作STS研究的「專利」,我更關心在此之前學者怎樣看待引領風騷的技術,看它們如何帶動社會想像與思考未來。提幾個過往的技術創新:令人不安的火車、神秘神奇的電話、見人所未見的X射線。它們的社會影響用「交引纏繞」(entanglement)之類的術語交代過去並無不可,但在文明進程的大格局裡,這樣的解釋似乎少了點人們對新興事物的好奇、激動與猶豫,那些直指人性,喚起希望的魅力。是這些讓科技得以進入技術社會的多元實作,交錯構成現代世界。
對此,STS研究的理論家拉圖(Bruno Latour)早在2000年訪問台灣時,便以「人類文明長程演化的模型」(Progress or Entanglement? — Two Models for the Long Term Evolution of Human Civilisation)為題,點出以技術社會為動力與基底的文明觀。文明不是新概念,甚至是有點政治不正確,「過時」的說法。但從拉圖眼中,它是以技術社會的核心,透過技能(skill and competence)獲得與分配,奠基於人為延續性(artificial continuity)的長期積累。在這個發展模型中技術與社會的纏繞不只發生在兩者的交轉(cross-over)之中,它們更把以技術統合的社會(technology are what makes the social realm hold together in the first place)兜轉前行,演化為今日所見的複雜社會(social complexity)。物(thing)一直都在,也不必然要汰舊方能換新。它們是新事物,科技研發的產物,但也是公共議題,社會論辯的主角。對拉圖而言,社會學者思考「社會如何看待技術」,或者STS研究者提問「技術裡有沒有社會」,都欠缺更高位、統整性的視點。唯有拋棄技術與社會對立的進步史觀,方可跳脫科學與宗教、全球化與地方的論證困局,精確掌握資本主義的社會表象(representation)。
以上文明觀看似復古,但對慣於追逐主流理論但疏於消化反省,長於學科課題但鮮少跨域對話的台灣學界來說,它直指將技術寫入社會,將社會納入技術的關鍵,凸顯出版《技術與社會理論》中文版的重要性。本書原屬Palgrave出版社「社會理論主題」(themes in social theory)」書系,作者是任教紐西蘭奧克蘭大學的Steve Matthewman。Matthewman的專長偏STS研究,課題包括災難與能源基礎建設,但他協同主持該校跨領域的「未來社會學群」(Social Futures Research Hub),關注社會學理論的發展,特別是傅柯與行動者網路理論(actor-network-theory, ANT)。《技術與社會理論》是他以技術串接社會學與STS研究,精要的理論複習,以下略記閱讀所見與大家分享。
《技術與社會理論》以技術的理論化(theorizing technology)為背景,大致以19世紀末到20世紀上半葉,以及戰後以降到1980年代的思想為軸心,開展技術社會的理論地景。前三章中社會學背景的讀者看到熟悉的馬克思、班雅明或愛里亞斯(Norbert Elias),但順著作者導引,也會遭遇法蘭克福學派學者,或者跨越到戰後,看到傅柯與質疑技術生產的諾布爾(David Noble)等。第四章到第六章集中於STS研究者對技術的觀點,部分該領域的開拓者,如溫納(Langdon Winner)、休斯(Thomas Hughes)、比克(Wiebe Bijker)與平奇(Trevor Pinch)等對台灣學界並不陌生。但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沒有全然用STS學科史的方式,透過孔恩或莫頓(Robert Merton),甚或用科學知識的社會學(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SSK)來介紹技術研究。相反地,這幾章中作者活用涂爾幹、愛里亞斯或紀登斯(Anthony Giddens)等學者,將技術研究納入社會學。雖然這幾章不見得能納入細微的STS理論轉折,比方說相對主義經驗綱領(empirical programme of relativism),但讀者一方面能瞭解STS研究者的理論爭議,一方面也透過人造物的政治(artifact,第四章主題)追索STS研究的發展,特別是ANT與傅柯對權力的看法與技術的道德向度等,讓它與社會學的理論轉向相互呼應。
第七與第八章作者透過社會學的事物轉向(thingly turn),將STS研究延伸進入帕深思(Talcott Parsons)提倡的群己關係(social relations)、文化研究,以至於後人類時代中的「社會賽伯格」(sociocyborg)。這裡有任教麻省理工學院STS博士課程,在心理學與社會學界都影響深遠的特克爾(Sherry Turkle)與她的人機研究,但更多的是社會學家所熟悉的思想家與文化研究學者,例如早期的涂爾幹與牟斯(Marcel Mauss),戰後的賽荷(Michel Serres)、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巴岱耶(Georges Bataille)、布迪厄(Pierre Bourdieu)、麥克魯漢(Marshall McLuhan)、賴許(Scott Lash)或哈洛威(Donna Haraway)等等。這裡作者雖然沒有特別標舉女性主義,但透過案例討論(如隨身聽與女性受眾的反應)與研究(如女性與高科技工作的探討),都呼應技術研究中不可忽視的性別因素(如技術史家卡溫[Ruth Schwartz Cowan]的經典案例)。基進點說,人機交融的「賽伯格」與多物種相伴的世界是現況描述,也是論述轉機。由資本主義推動,鎖定個人來研發的技術與裝置固然動搖公與私的界線,但它們也具有培力(empowerment)的可能,端看使用者的想法與實作。如書中引用哈洛威的洞見:「技術為了某些目的而重新安排這個世界,但是超越了功能與目的而邁向某些開放的東西,某些尚未存在的東西」。
這個看似不很社會學的「後人類宣示」點出STS研究對社會學的可能貢獻:如果社會解釋是與社會現實相關,但又非如實呈現的論述存在,那STS研究顯然透過技術,示現這個論述的力道與改變可能。如作者所言:「我們運用技術來解構我們的世界,我們以技術來操演我們的現實。接著,技術操演了我們。它們是社會變遷和社會穩定的能動者,協助生產了自我和社會。據此,它們是秩序的形式與生活的形式」。這是本書結論套用拉圖名著《我們從未現代過》(余曉嵐、林文源、許全義翻譯,群學,2012再版)的書名句型,但若翻轉為「我們從來都是後人類」(we have always been posthuman)的巧思,也是社會學與STS研究理論可以相互融通,探索未來的邀請。
作為導論性讀本,《技術與社會理論》拿捏社會學大論述與零散分歧的STS研究之間的平衡,尊重人文社會科學的思想源流並兼顧新興議題的概念銜接,論述清晰,內容充實。特別是後半部作者以具體研究來演繹概念,各章附有進階讀物,幫助讀者瞭解理論的進展與爭議,是其優點。值得一提的是,雖然以英語世界讀者為對象,但作為立基紐澳的學者,作者不僅放入STS研究的知名理論家,如拉圖或羅(John Law),也用相當篇幅挑選介紹較少為社會學界所知的研究者,如韋恩(Brian Wynne)與賽茲涅瓦(Olga Sezneva),或較少被視為理論家的運動者,如戴維斯(Mike Davis),顯示其獨特品味。
對台灣讀者來說,《技術與社會理論》涵蓋不少學者與理論,但畢竟有取捨的難處,比方說提出網路社會與流動空間,頗具影響力的社會學家柯斯特(Manuel Castells),或《老科技的全球史》(The Shock of the Old: Technology and global history since 1900)的作者,亦即提出技術使用觀點的技術史家艾傑頓(David Edgerton)等,書中僅點到為止。此外,對於筆者關注醫療與社會中的技術,STS研究者有不少創見,但或許顧及論述架構,或因為受限於出版年份(原書出版於2011年),也遭割愛。比方說,學界近年廣為引用,《照護的邏輯》(The Logic of Care: Health and the Problem of Patient Choice)的作者莫爾(Annemarie Mol),書中僅討論她的早期著作,而與生醫技術相關的社會人文學者,比方說,提出後基因體時代生命意義與生命政治的拉比諾(Paul Rabinow)或羅斯(Nikolas Rose),也付之闕如。在翻譯方面,領銜的王志弘是此間知名的理論研究者與引介者,兼具STS研究訓練,在內容理解上沒有問題。唯本書橫跨相當領域,牽涉諸多學者,不免部分人名與概念未及參照台灣慣例,讀者或可留意。
最後藉此機會談談在21世紀閱讀理論的意義。我們不會認為理論無用,但究竟《技術與社會理論》只能用在社會學專論課程,作為大學部的進階讀物,還是作為STS研究的外延讀物,用在研究所呢?對此,我希望用「理論的時代意義」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本書中引用米爾斯(C. Wright Mills)和傅柯的「當下的歷史」說法,提醒理論研究者技術之於當今社會的關鍵性意義。但換個角度想,當社會學理論正典化,逐漸脫離所處的發想情境與學術脈絡時,技術也提供讓它們「重生」的機會,讓這一代讀者透過研究問題與案例,再次體會它們在方法論上的立場、解釋力與限制。
雖然STS研究不是社會學主流,但拉圖確實因為這個新興領域的刺激,創造出影響20世紀後半以至於21世紀思潮的分析框架。謹以此文紀念這位天不假年的理論家,也盼望台灣讀者透過《技術與社會理論》超越學科畛域,開創更貼近周遭、有學有術、兼容並蓄的技術社會論述。
內文 : 第八章 客體生活:物與社會理論
和先前的其他人(Baudrillard、Serres)一樣,米勒(Miller)總結道,我們會在我們的物體中找到自己。米勒和涂爾幹與牟斯的差別,在於米勒是在經驗上通過田野研究才得到這個結論。涂爾幹、牟斯和米勒探討了團結如何以物質形式構成,以及我們如何通過物來定位自己和他人。即使如此,米勒想要跟涂爾幹派的社會科學保持距離,而且不只是在方法論上區分。涂爾幹的研究忠於世俗啟蒙思想的精神。他主張我們可以創造神,以便創造秩序。失去了宗教信仰,就需要以信奉某種其他的超越性物體來彌補。對涂爾幹而言,這個物體就是社會。漸增的個人主義和消費主義,導致了社會可能會碎裂崩毀的恐懼。米勒發現,像是社區與社會這類大型物體,對於他所探討的倫敦人而言,無關緊要。宗教或社會都不是主要的關切,它們也不是過著有秩序生活的先決條件。米勒相信「這形同拒絕了大部分的涂爾幹論點,以及社會科學的最初前提」。
物的社會生活I:技術生命週期
前一節的最主要論點是,技術給予我們穩定性,但我們的技術有多穩定?布朗(Bill Brown)指出,很明顯的,「無論物體在物質上看起來有多麼穩定,它們……在不同場合是不同的東西」。其實,我們在第一章已經說了很多,我們還以奶瓶為例來說明。檢視過物在社會生活中的位置,我們現在來考察物的社會生活。
史特林(Bruce Sterling)針對電話檢視了技術生命週期。他說,技術經歷了四個階段,從最初的「問號」到最後的死亡。第一個技術階段稱為「黃金霧體」(Golden Vaporware)階段。在這個階段,技術只是觀念上的。它只不過是一個想法、夢想或慾望,是發明者想像的虛構。史特林認為這位原型的發明者是貝爾(Alexander Graham Bell)。貝爾發明了許多奇幻設備,包括利用取自屍體的一隻耳朵的聲波記振儀(phonautograph)。這個人類機器混合體可以在煙燻玻璃上記錄聲波圖像。我們很少人聽過聲波記振儀。它的生命,就像大部分技術一樣,中斷了。大部分技術都始於且結束於黃金霧體。
如果技術確實設法進展到第二個階段,它們就成了崛起之星。史特林稱呼這是「滑稽的原型」(Goofy Prototype)階段。貝爾最偉大的精巧裝置,電話,在1876年3月10日達到了這個地位。貝爾在這一天創造歷史,率先將人類聲音通過電子方式傳輸。在這個階段,技術依然是不固定且不可靠的,它們的真正潛力還有待實現,它們的意義還有待固著。沒有人可以肯定它們的真正價值。如果這項技術要能夠從滑稽原型邁向更穩定的某種東西,還需要正面宣傳和財務投資。這令追加的研究和開發成為可能。在貝爾的案例中,電話在各處商展上吹捧,並在通俗刊物上廣受報導。貝爾的助理會在另一個房間演奏樂器,最後是在另一個城市演奏。觀眾可以清楚聽到曲調,雖然衝擊不總是正面的。沒有身軀的機械聲音,聽起來可能很怪異。
貝爾設想電話成為大眾媒介。音樂、佈道和演說將會傳播給位於網絡中的人。這對於潛在顧客而言頗為合理,雖然這種作法實現的唯一地方是在布達佩斯(Budapest)。他們的先驅(Hirmondó)系統經營了數十年,播放新聞、小說、戲劇和音樂會。從我們的觀點看,先驅看起來比較不像是電話的先鋒,反而比較像是今日電腦佈告欄的先祖。
貝爾的系統要勝出,就必須成功對付已經建立且十分勝任的電報系統。在許多方面,電報產業在競爭上領先:電報訊息可以留下恆久的痕跡,而且可以在接受者空閒的時候回應,它能夠比電話涵蓋更遠的距離,而且整個系統都已經建立完善。1858年,有一條電纜連結了美國與歐洲,到了1861年,電報線橫越了美國(McLuhan, 2001, p. 272)。史特林指出,1876年美國有214,000英哩的電報線,涵蓋了8,500個電報辦公室。相較於此,貝爾的設備看起來像個玩具,只會引起短暫興趣、有點意思的新鮮東西。
史特林稱第三個階段為金牛(Cash Cow)。在這個階段,技術成年了,新奇找到了效用,它將自身鑲嵌進入世界。貝爾的勝利來自於成功的重新命名。電話可以是一種私密技術,是人與人溝通的工具。這個機器不會主導,將相同的訊息傳送給大眾,而是由使用者來控制。他們會決定這項技術如何使用。沿著這些線索來行銷電話,對於它的成功非常重要。隨著使用者的數量增加、更大的涵蓋範圍,以及運用攻擊性的法律訴訟來牽制競爭者(總共600個案件,百分之百勝訴),電話達到了成熟。
成熟之後是死亡,技術的最後階段。迄今為止,這還不是電話的命運。在地球的許多地方,固網現在可能正讓位給行動電話,但是「全球電話系統是世界最大且最複雜的機器」。即使如此,有很多媒體已經走上了這條路,包括布達佩斯的電話先驅(Telefon Hirmondó)、費納奇鏡(phenakistocscopes)、立體感幻燈機(stereopticons)、西洋鏡(zoetropes)、八軌帶(8-track tapes)和磁片。事實上,由於數量眾多,史特林(Sterling)還發表了一份死亡媒介宣言(Dead Media Manifesto)。後來的一次訪談中,他解釋他的死亡媒介計劃(Dead Media Project)設計,是要彌補我們只聚焦於當前成功技術的扭曲圖像。比較新的技術不見得更好,唯一確定的是你必須付費升級(而且你很可能就停留在這個升級的跑步機上)。哎呀,這個計劃似乎終結了,它的連結也都失效了。史特林在班雅明那邊找到了旅伴,後者深信要通過篩查我們物質文化的廢棄物才能夠理解它。誠如賴許(Scott Lash)所說的,「班雅明在他的後期著作中,開始將現代性理解為一個死物的世界」(參見第三章)。
死掉的技術會發生什麼事?史特林認為它們就是從我們的記憶中淡出。然而,這不是唯一的可能性。邊緣物體可能作為古物而復活。在此,它們在室內設計的社會學中扮演要角,牽涉了特殊的文化氣氛,是材料、形式和空間演出的一部分。它們不再具有任何直接工具性意義的功能,但依然從事有價值的象徵工作:承擔見證、定錨記憶、調整心境。對布希亞(Baudrillard)而言,古物最重要的一點在於表意(signify)了時間。在物體的系統中,古物在心理上占有優位。人們尋找先前時代的人造物,因此也就是尋找他們自己文化脈絡以外的物品。這與對於真實性(authenticity)的索求緊密相關。(觀光也是一種時間旅行,具有相同性質。)「古物所回應的要求,乃是對於明確或完整實現的存有的要求」。獲取古物時,擁有者試圖經歷時間,甚至超越時間。古物將我們定錨於起源神話,它們中介了過往。古物擁有雙重功能,既連結到對起源的渴求,也固著於真實性。古物帶領我們回到什麼?傳統、原初智慧、神……以及真實性?這是連結上對確定性的需求。古物屬於某個富裕、知名或有權勢的人?若是如此,就會賦予它額外的價值。在這裡,我們有兩種互為對比的傾向。來自過往的古物,意味了時間的空洞性。它將我們錨定於它,藉此回溯時間,意味了存有的空洞性。這裡有某種逃避主義在運作。存有總是「在他方」,古物容許有限度的逃離我們的時代,脫離日常生活。這是它們神話性質的必要部分。
布希亞在西方人對於過往歲月物件的追尋,以及低度開發地區對於西方現代性技術產品的渴求之間,發現了類比之處。船貨崇拜可能令西方人感到可笑,但是布希亞發現對古物的愛好也是類似現象。在兩種情況中,我們談論的都是具有最低功能與最高意義的技術。「在兩種情況中,在物體形式下獲取的東西都是一種『好處』;『野蠻人』獲得現代技術,『文明』人獲取祖傳的意義」。兩者都展現了拜物教,前者為了權力,後者為了物體。我們所不是的東西投射進入了物品。物體拜物教經常用來當成推進的工具。在這裡,物成為我們社會地位的指標。現代社會愈來愈是這種情況,因為舊有的地位標誌如出身、血緣和家庭逐漸衰弱,雖然物可以用來鞏固這些鏈結。布迪厄寫道:
嚴格來說,每個物質傳承也都是文化傳承。家傳寶物不僅銘記了世系的年代和連續性,也神聖化了其社會身分,而這無法與歷經歲月的恆久性分離;它們也以特殊方式裨益於世系的精神再生產,也就是傳遞作為資產階級王朝之合法成員基礎的價值、美德和能力。在與古代物體的日常接觸時,像是經常拜訪古物經銷商和藝廊,或者更簡單的在一個「就在那兒」的熟悉、親密的,如同里爾克(Rilke)所說的,「誠實、良好、簡單、確定的」物體世界裡走動,得到的是某種「品味」,而這不是別的,就是與品味之物的緊密熟稔關係……這是一種緊密的依附,位於習癖的最深層次,依附於愛好與厭惡、同情與反感、想望與懼怕,而這比起公開的意見,更能塑造某個階級的無意識統一性。
準客體:後人類主義與同伴物種
史諾(C.P. Snow)主張有兩種文化區隔了現代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關注的是沒有人的物質世界,人文則聚焦於沒有物質性的人類世界。這有助於解釋社會理論為何不願意處理物體。後人類主義者發覺這兩種取徑都令人不滿意;他們嘗試理論化「物質和人類於同一個知識架構中」。如前所述,這涉及了令人類離開他們作為原動力(primum mobile)的優越位置。這類研究的一個早期例子是拉圖(Latour, 1988b)的《法蘭西的巴斯德化》(The Pasteurization of France,按:台灣版譯為《巴斯德的實驗室》),凸顯微生物作為社會行動者。他將其中一部分命名為,「我們比我們料想的還要多」(There Are More of Us Than We Thought)。這似乎是後人類主義的合適箴言,引進了眾多的非人類他者,像是拉圖(Latour)的微生物、減速丘和旅館鑰匙(參見第六章)、哈洛威(Haraway)的靈長目和狗,以及富蘭克林(Adrian Franklin, 2006)的桉樹。於是,很顯然,後人類主義者拒絕了將自然、生物與物件割讓給自然科學的知識分工。對他們而言,人類無法孤立於非人類世界之外。必須對物質性的問題寄予嚴肅關注。如富蘭克林(Franklin, 2007)指出的,這伴隨著某些取徑,它們「比較不關心物件(對於人類來說)意味了什麼,而是物件做了什麼」。如此一來,這就標示了與社會學傳統的斷裂,也就是從韋伯(Max Weber)(現象學取徑、社會建構論、芝加哥學派、俗民方法論)到關注物件對人類而言有何意義的取徑。意向性(intentionality)是根本議題。在針對標準社會理論提出重大挑戰時,拉圖和其他人宣稱,這並非人類的專屬領域。
後人類主義者傾向於主張所有物體都有能動性,因為它們在物質上會影響其他物質。物體包含了其他積極的物體。羅斯(Dan Rose,)說,也許我們應該拋棄本質的觀念。也許本質並不存在。比較好的想法是會變動的存有和多重的能動性。巴拉德(Karen Barad)也同意:「物質是內在積極流變的實體──不是物,而是……能動性的凝結」。因此,後人類主義者拒絕信守文化與物質的標準二元區分。他們斷然拒絕文化是積極且歷史性的,而物質是消極且不會變化的這種論斷。將人類對比於物質說不通,因為人類是由物質構成的,而且人類的生活完全鑲嵌於物質中。(關於這一點的早期「前-後人類主義」表述,參見Merlau-Ponty, 1968, p. 138)。巴黎不是只有人,無論是巴黎人、訪客或觀光客。拉圖與赫爾曼(Hermant)引述城市街道家具委員會(Commission municipale du mobilier urbain)的街道家具名錄。他們堅稱城市的成員也包括:「700個廣告柱、400個報攤、2個劇院櫃台、700個廣告牌、2000個資訊櫃台、400間公共廁所、1800個公車亭、9000個停車收費器、10000個交通號誌、2300個郵筒、2500個電話亭、20000個垃圾桶,以及9000張長椅」。它們被納入不只是因為它們和巴黎的人類共居者占有同一空間,而是因為它們參與且協助塑造了人類的行為:「這些不起眼物體的每一個……都帶來特殊的秩序,獨特的歸因,某種權威或禁制,承諾或允許」。
巴拉德(Barad)也解釋後人類主義是嘗試從世界的再現式理解,轉移到操演式理解,從現實如何描述轉移到現實如何達成。有時候,這會以另一種來自技術研究的說法來掌握:存有論政治,亦即「世界上有什麼東西的政治」。存有論政治由莫爾(Annemarie Mol)引入理論詞彙。它的知識起源要歸功於ANT,後者展示了社會的實際建構,亦即現實如何經由操演而存在,遂啟發了這類研究。於是,政治和現實是共同塑造的。其中一方是另一方促成的。從這些揭示學得的教訓是,現實存在於多重狀態。這意味了我們有選擇。要操演哪一種?它可以在哪裡操演?誰來選擇?就像技術開發一樣,有選項,事情可以改變,可以有不同的情況。存有論政治既呼籲要承認多樣性,也要尊重多樣性。
現實必須在實作中,於時間面、文化面和物質面建造而成。在STS,實驗室被視為是這麼做的主要場所。肽(TRF(H))、電腦、電話,或基因改造實驗鼠(OncoMouse™),從那裡釋放到世界上,或者沒有。這些物體運送了各種新現實與新存有論。這裡對於多元性(plurality)的強調,也解釋了為何像「建構」這類舊字眼失去了力道。在建構論者的說明裡,多元性總是過往的事物。由於相關社會群體帶來的封閉機制,現在是單一性占了上風。相對於此,存有論政治的支持者主張,現實經歷著各種類型工具的持續操縱。「這裡它被一把手術刀切進去;在那裡它被超音波轟炸;還有其他地方,再往下一點,它被放在天平上秤重」。
[…]對於操演性的強調標誌了脫離單純的字詞,邁向字詞、物件、動物、自然,實際上是廣大的物質性。這也標示了對於狀態的不滿,以及偏愛過程、論述實作和時間迸現。後人類主義的語言偏好動詞勝過名詞,而「做」和「變成」位列頂端。於是,比起物質化(materialization),物質(matter)沒那麼重要。在這種混攪(mangling)中,有個傾向是混合原來以破折號和斜線區分開來的東西,像是社會-技術變成社會技術(sociotechnical),自然/文化變成了「自然文化」(naturecultures),自然的與社會的變成「自然社會的」(naturalsocial)。這是表示貶抑舊的存有論區分的另一種方式。就此而論,哈洛威(Haraway)的〈賽伯格宣言〉(Cyborg Manifesto)格外重要,質疑了人與動物、人與機器,以及實體與非實體的區分。跟賽伯格──也就是軍事-科學-工業複合體的冷戰鬥士率先夢想的模控有機體──相同,同伴物種(companion species)也以新穎而無法預期的方式,匯集了文化與自然、人類與非人,以及有機與技術。
哈洛威對於分類向來很感興趣,關注類別如何建構和出現,以及它們如何協助操作我們。她對於物化這些界線或巡視它們,則毫無興趣。在許多方面,她的事業是由她對於跨越自然/文化區分的那些事物的興趣來定義的:賽伯格、郊狼,基改實驗鼠,以及女男人。狗很有趣,因為牠們跨越了許多圖式:寵物、朋友、食物來源、放牧者、獵者、害物、疾病攜帶者、研究對象、武器、保護者、救援者、追蹤者。換言之,牠們「是眾多類型的實體……〔具有〕各種類型的關係性」。這裡的關係性論點非常關鍵。如哈洛威所說的,「主體、客體、類型、種族、物種和性別,都是它們關聯的產物」。
最佳賣點 : STS×社會理論,迸出哪些新滋味?
眾多技術物案例,捕捉社會與「非人類」的交引纏繞
人類世時代必讀的科際研究入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