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論
| 作者 | 朱光潛 |
|---|---|
| 出版社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 商品描述 | 詩論:中西匯通的詩歌美學思想朱光潛看重詩:「要養成純正的文學趣味,最好從詩入手。能欣賞詩,自然能欣賞小說、戲劇等文學種類。」1931年前後,正在法國讀書的朱光潛,完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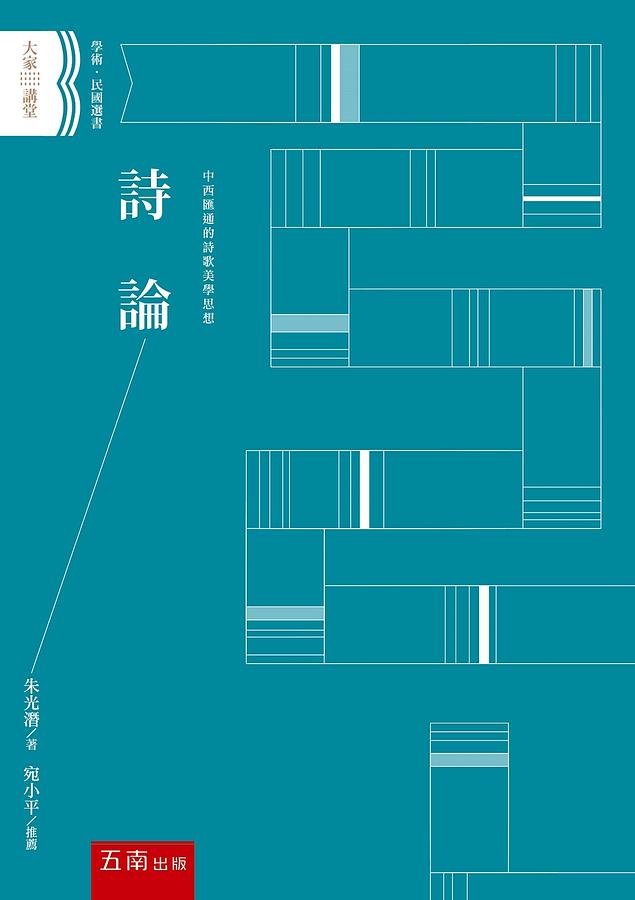
| 作者 | 朱光潛 |
|---|---|
| 出版社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 商品描述 | 詩論:中西匯通的詩歌美學思想朱光潛看重詩:「要養成純正的文學趣味,最好從詩入手。能欣賞詩,自然能欣賞小說、戲劇等文學種類。」1931年前後,正在法國讀書的朱光潛,完 |
內容簡介 中西匯通的詩歌美學思想 朱光潛看重詩:「要養成純正的文學趣味,最好從詩入手。能欣賞詩,自然能欣賞小說、戲劇等文學種類。」 1931年前後,正在法國讀書的朱光潛,完成《文藝心理學》。之後著手探討詩歌,撰寫《詩論》的綱要。1933年先後在北京大學、武漢大學開授《詩論》課程。他將講稿內容進行多次修改,在1943年初版,1984年是最後一次修訂,印行至今。書中講述詩的起源、詩的境界,以及與散文、音樂、美術的區別和聯繫,並對中國舊體詩的節奏、聲韻等問題作詳盡的分析。 作者在後記寫道:「在我過去的寫作中,自以為用功較多,比較有點獨到見解的,還是這本《詩論》。我在這裡試圖用西方詩論來解釋中國古典詩歌,用中國詩論來印證西方詩論;對中國詩的音律,為什麼後來走上律詩的道路,也作了探索分析。」 書末附錄三篇:〈給一位寫新詩的青年朋友 〉、〈詩的實質與形式〉(對話)、〈詩與散文〉(對話)。
作者介紹 朱光潛朱光潛(1897.9.19—1986.3.6)筆名孟實,安徽桐城人。是當代著名美學家,中國現代美學的開拓者和奠基者之一。早年受康德、黑格爾、克羅齊的主觀唯心主義思想的影響。著有《文藝心理學》介紹了西方美學史上的各家學說、《談美》、《給青年的十二封信》等。他在著述的同時,翻譯大量美學方面的經典著作,如黑格爾的《美學》、萊辛的《拉奧孔》、《柏拉圖文藝對話集》等。
產品目錄 推薦序 宛小平 抗戰版序 增訂版序 第 一 章 詩的起源 第 二 章 詩與諧隱 第 三 章 詩的境界—情趣與意象 第 四 章 論表現—情感思想與語言文字的關係 第 五 章 詩與散文 第 六 章 詩與樂—節奏 第 七 章 詩與畫—評萊辛的詩畫異質說 第 八 章 中國詩的節奏與聲韻的分析(上):論聲 第 九 章 中國詩的節奏與聲韻的分析(中):論頓 第 十 章 中國詩的節奏與聲韻的分析(下):論韻 第十一章 中國詩何以走上﹁律﹂的路(上):賦對於詩的影響 第十二章 中國詩何以走上﹁律﹂的路(下):聲律的研究何以特盛於齊 梁以後? 第十三章 陶淵明 附 錄 給一位寫新詩的青年朋友 詩的實質與形式(對話) 詩與散文(對話) 後 記
| 書名 / | 詩論 |
|---|---|
| 作者 / | 朱光潛 |
| 簡介 / | 詩論:中西匯通的詩歌美學思想朱光潛看重詩:「要養成純正的文學趣味,最好從詩入手。能欣賞詩,自然能欣賞小說、戲劇等文學種類。」1931年前後,正在法國讀書的朱光潛,完 |
| 出版社 /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 ISBN13 / | 9789577638106 |
| ISBN10 / | 9577638104 |
| EAN / | 9789577638106 |
| 誠品26碼 / | 2681874826002 |
| 頁數 / | 368 |
| 開數 / | 25K |
| 注音版 / | 否 |
| 裝訂 / | P:平裝 |
| 語言 / | 1:中文 繁體 |
| 級別 / | N:無 |
推薦序 : 推薦序
「在我過去的寫作中,自認為用功較多比較有點獨特見解的,還是這本《詩論》。」這是祖父經過近半個多世紀的學術沉澱,對自己著述作的一個冷靜估價。《詩論》的初稿也是祖父一九三三年回國進北京大學執教,交給胡適審閱的學術資歷憑證。自一九四三年初版(全書十章),到一九四八年增訂版(增收〈中國詩何以走上律的路〉),再到一九八四年重版(增補〈中西詩在情趣上的比較〉和〈替詩的音律辯護〉兩篇,〈陶淵明〉,共三章),這本書自問世讚譽之聲不絕於耳。張世祿稱祖父這本書「這就接受外來的學術而言,可以說是近於消化的地步。」(《評朱光潛〈詩論〉》載《國文月刊》,一九四七年第五十八期)近人勞承萬稱:「至今在中國詩壇,也沒有任何一本詩學理論可以與《詩論》相匹比者。」(《朱光潛美學論綱》,安徽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第一七一頁)
「抗戰版」《詩論》各章內容要旨及其內在關聯如下:第一章探尋詩的起源,以詩、樂、舞同源,三位一體加以揭示。第二章考察詩與詼諧、隱語、文字遊戲的關係。第三章討論詩的境界乃是「情趣與意象的契合」的命題,分梳幾種關於詩境的差別。第四章從情感思想與語言文字一致的關係出發,既繼承又改造了克羅齊的表現說,提出自己的思言一致的表現說。第五、六、七章依次分辨詩歌與散文、與音樂、與繪畫的連繫與區別,提出「詩是有音律的純文學」;指出詩的命脈「節奏」兼有純形式的和語言的兩方面;對萊辛的詩畫異質說進行了批評。第八、九、十章從聲、頓、韻三個方面分析中國詩的節奏和聲韻的特點,替詩的音律辯護,回應當時關於新詩的節奏和音律的論爭。
讀《詩論》的要義何在呢?其實祖父在「抗戰版」序裡有提示:「中國向來只有詩話而無詩學,……詩話大半是偶感隨筆,信手拈來,片言中肯,簡練親切,是其所長;但是他的短處在零亂瑣碎,不成系統,有時偏重主觀,有時過信傳統,缺乏科學的精神和方法。」而祖父寫《詩論》就是要將詩的(美的)科學建立起來,這和「詩話」、「詩品」、「詩說」離之千里。所以他才在第三章裡對王國維「詩境」的「有我之境」和「無我之境」發難。說到「根」處,還是覺得這種詩論猶如「霧裡看花」籠統而缺少科學分析精神。祖父用「同物之境」和「超物之境」的「詩境」說替代王國維的「詩境」說,並不是對王氏的澈底否定,而是引入情趣與意象「二元」互動的分析(科學的)結構,強調了情趣與意象的「往復回流」中詩人所達到的「冷靜中的回味」。這就深化了我們對「詩境」的認識。且不說王國維《人間詞話》還脫不去傳統的點評的詩話體例;就是說到現代詩學並稱為「四大詩論」的朱自清、廢名、艾青,在我看來都還沒有達到祖父這部《詩論》的美學高度和深度。這些論者多少都存有祖父說的那樣一種偏見:以為詩的精微奧妙可意會而不可言傳,如經科學分析,則如七寶樓臺,拆碎不成片段。所以常常可能會有人拿著中國傳統講的「言有盡而意無窮」來向祖父拷問:認為你朱光潛一方面批評王國維太重「顯」,沒有注意到詩的妙味恰恰在於「隱」;另一方面你朱光潛又在《詩論》第四章裡步克羅齊後塵把思想和語言看作是一回事,那這個「隱」又如何表達呢?你朱光潛不贊成「意在言先」、「意內言外」,使得傳統言不盡意、意在言外的內容發生改變,你這不是否定了言不盡意的傳統說法嗎?
否,我們在《詩論》(第四章)裡不是明明白白看到寫著:「我們把情感思想和語言的關係看成全體和部分的關係,這一點須特別著重。全體大於部分,所以情感思想與語言雖平行一致,而範圍大小卻不能完全疊合。……但是情感思想之一部分有不伴著語言的可能。……情感中有許多細微的曲折起伏,雖可以隱約地察覺到而不可直接用語言描寫。這些語言所不達而意識所可達的意象思致和情調永遠是無法可以全盤直接的說出來,好在藝術創造也無須把凡所察覺到的全盤直接的說出來。詩的特殊功能就在以部分暗示全體,以片段情景喚起整個情景的意象和情趣。詩的好壞也就看它能否實現這個特殊功能。以極經濟的語言喚起極豐富的意象和情趣就是『含蓄』、『意在言外』和『情溢乎詞』。嚴格地說,凡是藝術的表現(連詩在內)都是『象徵』(symbolism),凡是藝術的象徵都不是代替或翻譯而是暗示(suggestion),凡是藝術的暗示都是以有限寓無限。」
祖父在一九八四年「三聯版」補的《後記》裡稱:「我在這裡試圖用西方詩論來解釋中國古典詩歌,用中國詩論來印證西方詩論;對中國詩的音律,為什麼後來走上律詩的道路,也作了探索分析。」
這種中西相互印證,相互闡釋的比較文學方法,祖父用的最早,也最熟練。這在《詩論》第七章中討論萊辛《拉奧孔》最有代表性。
祖父舉出萊辛「舉世公認」貢獻:一是對詩畫同質說「籠統的含混」作了「近於科學的」清洗。二是「在歐洲第一個人看出藝術與媒介(如形色之於圖畫,語言之於文學)的重要關聯。」「萊辛在一百幾十年以前彷彿就已經替克羅齊派美學下一個很中肯的針砭了。」三是「萊辛討論藝術,並不抽象地專在作品本身著眼,而同時顧到作品在讀者心中所引起的活動和影響。比如他主張畫不直接選擇一個故事的興酣局緊的『頂點』,就因為讀者的想像無法再向前進。」同時,也批評萊辛:其一,「他對於藝術的見解似乎是一種很粗淺的寫實主義。」其二,萊辛依「藝術美模仿自然美」這個信條推演出「美僅限於物體」,而詩根本不能描寫物體,則詩中就不能有美。其三,萊辛雖然注意到藝術作品和媒介的連繫,但他沒有注意到後來像克羅齊所說的藝術的「整一性」問題,結果將「詩」與「藝術」對立起來了,只承認藝術有形式的美,而是詩則只能是「表現」(指動作的意義,與美不能有直接的關係)。其四,萊辛誇大了詩與畫的界限。其五,萊辛對於山水花卉翎毛的輕視不符合中國畫的創作旨趣。其六,萊辛說詩一定不能描寫並列的事物也過於絕對。祖父舉馬志遠〈天淨沙〉:「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王維〈送使至塞上〉:「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等句作證明並非如萊辛所說物象不能並存。
在《詩論》第八、九、十章分析中國詩節奏與聲韻特點後,祖父在第十一、十二章揭示了中國詩體中最具有民族特色的律詩演化軌跡及成因。其實,他的意圖並非在找尋或揭櫫某個特定文學體裁的興起成因,倒不如說是想藉助中國詩由古體向近體詩演變的這一歷史現象,以豐贍的詩史事實和廣闊的中西比較的視野,力圖把特定文學史現象納入他們各國詩歌音義離合的普遍公式中,從詩歌形態的生成視角進一步申論詩歌的本體,使之具有美之科學的高度。
以上我只是循著祖父已有「序」的提示作了申論,讀者想探詩理的究竟,怕最好的方式還是細讀原著。
宛小平
二○二○年元月十八日
於安居苑忘適齋
自序 : 抗戰版序
在歐洲,從古希臘一直到文藝復興,一般研究文學理論的著作都叫做詩學。「文學批評」這個名 詞出來很晚,它的範圍較廣,但詩學仍是一個主要部門。中國向來只有詩話而無詩學,劉彥和的《文心雕龍》條理雖縝密,所談的不限於詩。詩話大半是偶感隨筆,信手拈來,片言中肯,簡練親切,是其所長;但是它的短處在零亂瑣碎,不成系統,有時偏重主觀,有時過信傳統,缺乏科學的精神和方法。
詩學在中國不甚發達的原因大概不外兩種。一般詩人與讀詩人常存一種偏見,以為詩的精微奧妙可意會而不可言傳,如經科學分析,則如七寶樓臺,拆碎不成片段。其次,中國人的心理偏向重綜合而不喜分析,長於直覺而短於邏輯的思考。謹嚴的分析與邏輯的歸納恰是治詩學者所需要的方法。
詩學的忽略總是一種不幸。從史實看,藝術創造與理論常互為因果。例如:亞里士多德的《詩學》歸納希臘文學作品所得的結論,後來許多詩人都受了它的影響,這影響固然不全是好的,也不全是壞的。次說欣賞,我們對於藝術作品的愛憎不應該是盲目的,只是覺得好或覺得不好還不夠,必須進一步追究它何以好或何以不好。詩學的任務就在替關於詩的事實尋出理由。
在目前中國,研究詩學似尤刻不容緩。第一,一切價值都由比較得來,不比較無由見長短優劣。現在西方詩作品與詩理論開始流傳到中國來,我們的比較材料比從前豐富得多,我們應該利用這個機會,研究我們以往在詩創作與理論兩方面的長短究竟何在,西方人的成就究竟可否借鑑。其次, 我們的新詩運動正在開始,這運動的成功或失敗對中國文學的前途必有極大影響,我們必須鄭重謹慎,不能讓它流產。當前有兩大問題須特別研究,一是固有的傳統究竟有幾分可以沿襲,一是外來的影響究竟有幾分可以接收。這都是詩學者所應虛心探討的。
寫成了《文藝心理學》之後,我就想對於平素用功較多的一種藝術—詩—作一個理論的檢討。在歐洲時我就草成綱要。一九三三年秋返國,不久後任教北大,那時胡適之先生掌文學院,他對於中國文學教育抱有一個頗不為時人所贊同的見解,以為中國文學系應請外國文學系教授去任一部分課。他看過我的《詩論》初稿,就邀我在中文系講了一年。抗戰後我輾轉到了武大,陳通伯先生和胡先生抱同樣的見解,也邀我在中文系講了一年《詩論》。我每次演講,都把原稿大加修改一番。改來改去,自知仍是粗淺,所以把它擱下,預備將來有閒暇再把它從頭到尾重新寫過。它已經擱了七八年,再擱七八年也許並無關緊要。現在通伯先生和幾位朋友編一文藝叢書,要拿這部講義來充數,因此就讓它出世。這是寫這書和發表這書的經過。
我感謝適之、通伯兩先生,由於他們的鼓勵,我才有機會一再修改原稿,朱佩弦、葉聖陶和其他幾位朋友替我看過原稿,給我很多的指示,我也很感激。
朱光潛
一九四二年三月於四川嘉定
增訂版序
這部小冊子在抗戰中由重慶國民圖書出版社印行過二千冊,因為錯字太多,我把版權收回來以後就沒有再印。從前我還寫過幾篇關於詩的文章,在抗戰版中沒有印行,原想將來能再寫幾篇湊成第二輯。近來因為在學校裡任課兼職,難得抽出功夫重理舊業,不知第二輯何日可以寫成,姑將已寫成的加入本編。這新加的共有三篇,〈中國詩何以走上「律」的路〉上下兩篇是對於詩作歷史檢討的一個嘗試,〈陶淵明〉一篇是對於個別作家作批評研究的一個嘗試,如果時間允許,我很想再寫一些像這一類的文章。
朱光潛
一九四七年夏於北京大學
內文 : 第十三章 陶淵明
淵明詩篇篇有酒,這是盡人皆知的,像許多有酒癖者一樣,他要借酒壓住心頭極端的苦悶,忘去世間種種不稱心的事。他嘗說「常恐大化盡,氣力不及衰,撥置且莫念,一觴聊可揮」,「泛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數斟已復醉,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為貴」,「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酒對於他彷彿是一種武器,他拿在手裡和命運挑戰,後來它變成一種沉痼,不但使他「多謬誤」,而且耽誤了他的事業,妨害他的病體。從〈榮木〉詩裡「志彼不舍(學業),安此日富(酒),我之懷矣,但焉內疚」那幾句話看,他有時頗自悔,所以曾有一度「止酒」。但是積習難除,到死還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淵明和許多有癖好的詩人們(例如:阮籍、李白、波斯的奧馬康顏之類)的這種態度,在近代人看來是「逃避」,我們不能拿近代人的觀念去責備古人,但是「逃避」確是事實。逃避者自有苦心,讓我們慶賀無須飲酒的人們的幸福,同時也同情於「君當恕醉人」那一個沉痛的呼聲。
世間許多醉酒的人們終止於劉伶的放誕,淵明由衝突達到調和,並不由於飲酒。彌補這世間缺陷的有他的極豐富的精神生活,尤其是他的極深廣的同情。我們一般人的通病是囿在一個極狹小的世界裡活著,狹小到時間上只有現在,在空間上只有切身利益相關係的人與物;如果現在這些切身利害關係的人與物對付不順意,我們就活活地被他們扼住頸項,動彈不得,除掉怨天尤人以外,別無解脫的路徑。淵明像一切其他大詩人一樣,有任何力量不能剝奪的自由,在這「樊籠」以外,發現一個「天高任鳥飛」的字宙。第一是他打破了現在的界限而遊心於千載,發現許多可﹁尚友﹂的古人。〈詠貧士〉詩中有兩句話透露此中消息:「何以慰吾懷,賴古此多賢。」這就是說,他的清風亮節在當時雖無同調,過去有同調的人們正復不少,使他自慰「吾道不孤」。他好讀書,就是為了這個緣故,說:「歷覽千載書,時時見遺烈」,而這些「遺烈」可以使他感發興起。他的詩文不斷地提到他所景仰的古人,〈述酒〉與〈扇上畫贊〉把他們排起隊伍來,向他們馨香禱祝,更可以見出他的志向。這隊伍裡不外兩種人,一是固窮守節的隱士,如荷蓧丈人、長沮、桀溺、張長公、薛孟嘗、袁安之類,一是亡國大夫積極或消極地抵抗新朝、替故主復仇的,如伯夷、叔齊、荊軻、韓非、張良之類,這些人們和他自己在身世和心跡上多少相類似。
在這裡我們不妨趁便略談淵明帶有俠氣,存心為晉報仇的看法。淵明俠氣則有之,存心報仇似未必,他不是一個行動家,原來為貧而仕,未嘗有杜甫的「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醇」那種近於誇誕的願望,後來解組歸田,終身不仕,一半固由於不肯降志辱身,一半也由於他慣嘗了「樊籠」的滋味,要「返自然」,庶幾落得一個清閒。他厭惡劉宋是事實,不過他無力推翻已成之局,他也很明白。所以他一方面消極地不合作,一方面寄懷荊軻、張良等「遺烈」,所謂「刑天舞干戚」,雖無補於事,而「猛志固常在」。
淵明的心跡不過如此,我們不必妄為捕風捉影之談。淵明打破了現在的界限,也打破了切身利害相關的小天地界限,他的世界中人與物以及人與我的分別都已化除,只是一團和氣,普運周流,人我物在一體同仁的狀態中各徜徉自得,如莊子所說的「魚相與忘於江湖」。他把自己的胸襟氣韻貫注於外物,使外物的生命更活躍,情趣更豐富;同時也吸收外物的生命與情趣來擴大自己的胸襟氣韻。這種物我的回響交流,有如佛家所說的「千燈相照」,互映增輝。所以無論是微雲孤鳥,時雨景風,或是南阜斜川,新苗秋菊,都到手成文,觸目成趣。淵明人品的高妙就在有這樣深廣的同情:他沒有由 苦悶而落到頹唐放誕者,也正以此。中國詩人歌詠自然的風氣由陶、謝開始,後來王、孟、儲、韋諸家加以發揮光大,遂至幾無詩不狀物寫景。但是寫來寫去,自然詩終讓淵明獨步。許多自然詩人的毛病在只知雕繪聲色,裝點的作用多,表現的作用少,原因在缺乏物我的混化與情趣的流注。自然景物在淵明詩中向來不是一種點綴或陪襯,而是在情趣的戲劇中扮演極生動的角色,稍露面目,便見出作者的整個的人格。這分別的原因也在淵明有較深厚的人格的涵養,較豐富的精神生活。
淵明的心中有許多理想的境界。他所景仰的「遺烈」固然自成一境,任他「托契孤遊」;他所描寫的桃花源尤其是世外樂土。歐陽公嘗說晉無文章,只有陶淵明的〈歸去來辭〉。依我的愚見,〈桃花源記〉境界之高還在〈歸去來辭〉之上。淵明對於農業素具信心,〈勸農〉、〈懷古田舍〉、〈西田獲早稻〉諸詩已再三表明他的態度。〈桃花源記〉所寫的是一個理想的農業社會,無政府組織,甚至無詩書曆志,只「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這境界頗類似盧梭所稱羨的「自然狀況」。淵明身當亂世,眼見所謂典章制度徒足以擾民,而農業國家的命脈還是繫於耕作,人生真正的樂趣也在桑麻閒話,樽酒消憂,所以寄懷於「桃花源」那樣一個淳樸的烏托邦。
淵明未見得瞧得起蓮社諸賢的「文字禪」,可是禪宗人物很少有比淵明更契於禪理的。淵明對於自然的默契,以及他的言語舉止,處處都流露著禪機。比起他來,許多談禪的人們都是神秀,而他卻是慧能。姑舉一例以見梗概。據《晉書‧隱逸傳》:「他性不解音,而蓄素琴一張,弦徽不具。每朋酒之會,則托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弦上聲。』」這故事所指示的,並不是一般人所謂「風雅」,而是極高智慧的超脫。他的胸中自有無限,所以不拘泥於一切跡象,在琴如此,在其他事物還是如此。昔人謂「不著一字,盡得風流」為詩的勝境,淵明不但在詩裡,而且在生活裡,處處表現出這個勝境,所以我認為他達到最高的禪境。慧遠特別敬重他,不是沒有緣由的。
總之,淵明在情感生括上經過極端的苦悶,達到極端的和諧肅穆。他的智慧與他的情感融成一 片,釀成他的極豐富的精神生活。他的為人和他的詩一樣,都很淳樸,卻都不很簡單,是一個大交響曲而不是一管一弦的清妙的聲響。
………
附錄:給一位寫新詩的青年朋友
朋友,你的詩和信都已拜讀。你要我“改正”並且“批評”,使我很慚愧。在這二十年中我雖然差不多天天都在讀詩,自己卻始終沒有提筆寫一首詩,作詩的辛苦我只從旁人的作品中間接地知道,所以我沒有多少資格說話。談到“改正”,我根本不相信詩可以經旁人改正,只有詩人自己知道他所寫的與所感所想的是否恰相吻合,旁人的生活經驗不同,觀感不同,縱然有膽量“改正”,所改正的也是另一回事,與原作無干。至於“批評”,我相信每個詩人應該是他自己的嚴厲的批評者。拉丁詩人賀拉斯勸人在作品寫成之後把它擺過幾月或幾年不發表,我覺得那是一個很好的忠告。
詩剛做成,興頭很熱烈,自己總覺得它是一篇傑作,如果你有長進的可能,經過一些時候冷靜下來,再拿它仔細看看,你就會看出自己的毛病,你自己就會修改它。許多詩人不能有長進,就因為缺乏這點自我批評的精神。你不認識我,而肯寄詩給我看,詢取哦的意見,這種謙虛我不能不有所報答,我所說的話有時不免是在熱興頭上潑冷水,然而我不遲疑,我相信誠懇的話,是一個真正詩人所能接受的,就是有時不甚入耳,也是他所能原宥的。你要我回答,你所希望於我的當然不只是一套恭維話。
我講授過多年的詩,當過短期的文藝刊物的編輯,所以常有機會讀到青年朋友們的作品。這些作品中分量最多的是新詩,一般青年作家似乎特別喜歡做新詩。原因大概不外兩種:第一,有些人以為新詩容易做,既無格律拘束,又無長短限制,一陣新血來潮,讓情感“自然流露”,就可以湊成一首。其次,也有一些人是受風氣的影響,以為詩在文學中有長久的崇高的地位,從事於文學總得要做詩,而且徐志摩、冰心、老舍許多人都在做新詩。
詩是否容易做,我沒有親切的經驗,不過據我研究中外大詩人的作品所得的印象來說,詩是最精妙的觀感表現於最精妙的語言,這兩種精妙都絕對不容易得來的,就是大詩人也往往須費畢生的辛苦來摸索。作詩者多,識詩者少。心中存這一分“詩容易做”的幻想,對於詩就根本無緣,做來做去,只終身做門外漢。
再其次,學文是否必須做詩,在我看,也是一個問題。我相信文學到了最高境界都必定是詩,而且相信生命如果未至末日,詩也就不會至末日。不過我相信每一時代的文學有每一時代的較為正常的表現方式。比如說,荷馬生在今日也許不寫史詩,陀斯妥耶夫斯基生在古代也許不寫小說。在我們的時代,文學的最常的表現的方式似乎是散文、小說而不是詩。這也並不是我個人的意見,西方批評家也有這樣想的。
許多青年白費許多可貴的精力去做新詩,幼稚的情感發洩完了,才華也就盡了。在我個人看,這種浪費實在很可惜。他們如果腳踏實地練習散文、小說,成就也許會好些。這話自然不是勸一切人都莫做詩,詩還是要有人做,只是做詩的人應該真正感覺到自己所感所想的非詩方式決不能表現。如果用詩的方式表現的用散文也還可以表現,甚至於可以表現得更好,那麼詩就失去它的“生存理由”了。我讀過許多新詩,我深切地感覺到大部分新詩根本沒有“生存理由”。
詩的“生存理由”是文藝上內容和形式的不可分性。每一首詩,猶如任何一件藝術品,都是一個有血有肉的靈魂,血肉需要靈魂才現出它的活躍,靈魂也需要血肉才具體可捉摸。假如拿形式比血肉而內容比靈魂,叫做“詩”的那種血肉是否有一種特殊的靈魂呢?這問題不象它現在表面的那麼容易。就粗略的跡象說,許多形式相同的詩而內容則千差萬別。
多少詩人用過五古、七律或商籟?可是同一體裁所表現的內容不但甲詩人與乙詩人不同,即同一詩人的作品也每首自居一個性。就內在的聲音節奏說,外形儘管同是七律或商籟,而每首七律或商籟讀起來的聲調,卻隨語言的情味意義而有種種變化,形成它的特殊的音樂性。這兩個貌似相反的事實告訴我們的不是內容與形式無關,而是一般人把七律、商籟那些空殼看成詩的形式是一種根本的錯誤。
每一首詩有每一首詩的特殊形式,是叫做七律、商籟那些模型得著當前的情趣貫注而具生命的那種聲音節奏;正猶如每個人有每個人的特殊面貌,而這種特殊面貌是叫做口鼻耳目那些共同模型得到本人的性格而具個性的那種神情風采。一首詩有凡詩的共同性,有它所特有的個性,共同性為七律、商籟之類模型,個性為特殊情趣所表現的聲音節奏。這兩個成分合起來才是一首詩的形式,很顯然的兩成分之中最重要的不是共同性而是個性。
七律、商籟之類軀殼雖不能算是某一詩的真正形式,而許多詩是用這些模型鑄就的卻是事實。這些模型是每民族經過悠久歷史所造成的,每個民族都出諸本能地或出諸理智地感覺到做“詩”的那一種文學需要巾幗這些模型鑄就。這根深蒂固的傳統有沒有它的理由呢?這問題實在就是:散文之外何以要有詩?依我想,理由還是在內容與形式的不可分性。七律、商籟之類模型的功用在節奏的規律化,或則說,語言的音樂化。情感的最直接的表現是聲音節奏,而文字意義反在其次。文字意義所不能表現的情調常可以用聲音節奏表現出來。詩和散文如果有分別,那分別就基於這個事實。
散文敘述事理,大體上借助於文字意義已經很夠;它自然也有它的聲音節奏,但是無須規律化或音樂化,散文到現出規律化或音樂化時,它的情趣的成分就逐漸超出理智的成分,這就是說,它逐漸侵入詩的領域。詩詠歎情趣,大體上單靠文字意義不夠,必須從聲音節奏上表現出來。詩要儘量地利用音樂性來補文字的不足,七律、商籟之類模型是發揮文字音樂性的一種工具。這話怎樣講呢?拿詩和散文來比,我們就會見出這個道理。散文沒有固定模型做基礎,音節變來變去還只是“散”;詩有固定模型做基礎,從整齊中求變化,從束縛中求自由,變化的方式於是層出不窮。
這話乍聽起來似牽強,但是細心比較過詩和散文的音樂性者都會明白這道理是真確的,詩的音樂性實在比散文的豐富反繁複,正猶如樂音比自然中的雜音較豐富繁複是一個道理。樂音的固定模型非常簡單——八個音階。但這八個音階高低起伏與縱橫錯綜所生的變化是多麼繁複?詩人利用七律、商籟之類模型來傳出情趣所有的聲音節奏,正猶如一個音樂家利用八個音階來譜交響曲。
新詩比舊詩難作,與那因就在舊詩有“七律”、“五古”、“浪淘沙”之類固定模式可利用,一首不甚高明的舊詩縱然沒有它所應有的個性,卻仍有凡詩的共同性,仍有一個音節的架子,讀起來還是很順口;新詩的固定模型還未成立,而一般新詩作者在技巧上缺乏訓練,又不能使每一首詩現出很顯著的音節上的個性,結果是散漫蕪雜,毫無形式可言。把形式做模型加個性來解釋,形式可以說就是詩的靈魂,做一首詩實在就是賦予一個形式與情趣,“沒有形式的詩”實在是一個自相矛盾的名詞。許多新詩人的失敗都在不能創造形式,換句話說,不能把握住他所想表現的情趣所應有的聲音節奏,這就不啻說他不能做詩。
你的詩不算成功——恕我直率——如同一般新詩人的失敗一樣,你沒有創出形式,我們讀者無法在文字意義上以外尋出一點更值得玩味的東西。你自以為是在做詩,實在還是在寫散文,而且寫不很好的散文,你把它分行寫,假如像散文一樣一直寫到底,你會覺得有很大的損失麼?我喜歡讀英文詩,我鑒別英文詩的好壞還有一個很奇怪的標準。一首詩到了手,我不求甚解,先把它朗誦一遍,看它讀起來是否有一種與眾不同的聲音節奏。如果音節很堅實飽滿,我斷定它後面一定有點有價值的東西;如果音節空洞淩亂,我斷定作者胸中原來也就很空洞淩亂。我應用這個標準,失敗時候還不很多。讀你的詩,我也不知不覺在應用這個標準,老實說,讀來讀去,我就找不出一種音節來,因此,我就很懷疑你的詩後面根本沒有什麼值得說的。從文字意義上分析了一番,果不其然!你對明月思念你的舊友,對秋風葉落感懷你的身世,你裝上一些貌似漂亮而實惡俗不堪的詞句,再“啊”地“呀”地幾聲,加上及格大驚嘆號,點了一行半行的連點,筆停了,你喜歡你做成了一首新詩。朋友,恕我坦白地告訴你,這是精力的浪費!
我知道,你有你的師承。你看過五四時代作風的一些新詩,也許還讀過一些歐洲浪漫時代的詩。五四時代作家和他們的門徒勇於改革和嘗試的精神固然值得敬佩,但是事實是事實,他們想學西方詩,而對於西方詩,根本沒有深廣的瞭解;他們想推翻舊傳統,而舊傳統桎梏他們還很堅強。他們是用白話寫舊詩,用新瓶裝舊酒。他們處在過渡時代,一切都在草創,我們也無用苛求,不過我們要明白那種詩沒有多大前途,學它很容易誤事。他們的致命傷是沒有在情趣上開闢新境,沒有學到一種嶄新的觀察人生世相的方法,只在搬弄一些平凡的情感,空洞的議論,雖是白話而仍很陳腐的辭藻。目前報章雜誌上所發表的新詩,除極少數例外,仍然是沿襲五四時代的傳統,雖然在表面上題材和社會意識有些更換。詩不是一種修辭或雄辯,許多新詩人卻只在修辭或雄辯上做功夫,出發點就已經錯誤。
五四時代和現在許多青年詩人所受到的西方詩影響,大半偏於浪漫派如拜倫、雪萊之流。他們的詩本無可厚非,他們最容易被青年人看成模範,可是也最不宜於做青年人的模範。原因很簡單,浪漫派的唯我主義與感傷主義的氣息太濃,學他們的人很容易作繭自窒,過於信任“自然流露”,任幼稚平凡的情感無節制地無洗練地和盤托出;拿舊詩來比,很容易墮入風花雪月憐我憐卿的魔道。詩和其他藝術一樣,必有創造性與探險性,老是在踏得稀爛的路軌上盤旋,決無多大出息。我對於寫實主義並不很同情,但是我以為寫實的訓練對於青年詩人頗有裨益,它可以幫助他們跳開小我的全套,放開眼界,去體驗不同的任務在不同的情境中所有的不同的生活情調。這種功夫可以銳化他們的敏感,擴大他們的“想像的同情”,開發他們的精神上的資源。總而言之,青年詩人最好少做些“洩氣”式的抒情詩,多做一些帶有戲劇性的敘述詩和描寫性格詩。他們最好少學些拜倫和雪萊,多學些莎士比亞和現代歐美詩。
提到“學”字,我可以順便回答你所提出的一個問題:做詩是否要多讀書?“學”的範圍甚廣,我們可以從人情世故物理中學,可以從自己寫作的辛苦中學,也可以從書本中學,讀書只是學的一個節目,一個不可少的而卻也不是最重要的節目。許多新詩人的毛病在不求玩味生活體驗,不肯耐辛苦去自己摸索路徑,而只在看報章雜誌上一些新詩,揣摩他們,模仿它們(“他們”與“它們”原文如此——編者注)。我有一位相當有名的做新詩的朋友,一身都在模仿當代新詩人(“一身”原文如此——編者注),早年學徐志摹,後來學藏克家,學林庚,學卞之琳,現在又學宣傳詩人喊口號。學來學去,始終沒有學到一個自己的本色行當。我很同情他的努力,卻也很惋惜他的精力浪費。
“學”的問題確是新詩的一個難問題,我們目前值得學的新詩範作實在是太少。大家象瞎子牽瞎子,牽不到一個出路。凡是沒有不學而能的,藝術尤其如此。“學”什麼呢?每個青年詩人似乎都在這問題上彷徨。伸在眼前的顯然只有三條路:第一條,是西方詩的路。據我看,這條路可能性最大。它可以教會我們儘量發揮語言的潛能。不過詩不能翻譯,要瞭解西方詩,至少須精通一種西方語言。據我所知道的,精通一國語言而到真正能欣賞它的詩的程度,很需要若干年月的耐苦。許多青年詩人是沒有這種機會,或是沒有這種堅強的意志。
第二條,是中國舊詩的路。有些人根本反對讀舊詩,或是以為舊詩變成一種桎梏,阻礙自由創造。我的看法卻不如此。我以為中國文學只有詩還可以同西方抗衡,它的範圍固然比較狹窄,它的精煉深永卻往往非西方詩所可及。至於舊詩能成桎梏的話,這要看學者是否善學,善學則到處可以討經驗,不善學則任何模範都可以成桎梏。每國詩過些年代都常經過革命運動,每種新興作風對於舊有作風都必是反抗,可是每國詩也都有一個一線相承、綿延不斷的傳統,而這傳統對於反抗它的人們的影響反而特別大。我想中國詩也不例外。很可能幾千年積累下來的寶藏還值得新詩人去發掘。
第三條,是流行民間文學的路。文學本起自民間,由民間傳到文人而發揮光大,而形式化、僵硬化,到了僵硬化的時代,文人的文學如果想復蘇,也必定從新興的民間文學吸取生氣。西方文學演變的痕跡如此,中國文學演變的痕跡也是如此。目前研究民間文學的提倡很值得注意和同情。不過民間文學與學西詩舊詩同樣地需要聰慧的眼光與靈活的手腕,呆板的模仿是誤事的。同時我們也不要忘記民間文學有它的特長,也有它的限制。像一般人所模仿的古書戲詞已不能算是真正的民間文學,它是到了形式化和僵硬化的階段了,在內容和形式上實多無甚可取,還有一部分人愛好它,並不是當作文學去愛好它,而是當作音樂去愛好它,拿它來做宣傳工具,固無不可;如果說拿它來改善新詩,我很懷疑它會有大成就。
大家在談“民族形式”,在主張“舊瓶裝新酒”,思想都似有幾分糊塗。中國詩現在還沒有形成一個新的“民族形式”,“民族形式”的產生必在偉大的“民族詩”之後,我們現在用不著談“民族形式”,且努力去創造“民族詩”。未有詩而先有形式,就如未有血肉要先有容貌,那是不可想像的。至於“舊瓶新酒”的比喻實在有些不倫不類。詩的內容與形式的關係並不是酒與瓶的關係。酒與瓶可分立;而詩的內容與形式並不能分立。酒與瓶的關係是機械的,是瓶都可以裝酒,詩的內容與形式的關係是化學的,非此形式不能表現此內容。如果我們有新內容,就必須創造新形式。這形式也許有時可從舊形式脫化,但絕對不能是呆板的模仿。應用“舊瓶”是朝抵抗力最低的路徑走,是偷懶取巧。
最後,新詩人常歡喜抽象地談原則,揣摩風氣地依傍門戶,結果往往於主義和門戶之外一無所有。詩不是一種空洞的主義,也不是一種敲門磚。每個新詩人應極力避免這些塵俗的引誘,保存一種自由獨立的精神,死心塌地地做自己的功夫,摸索自己的路徑,開闢自己的江山。大吹大擂對於詩人是喪鐘,而門戶主義所做的勾當卻是大吹大擂。
朋友,這番話,我已經聲明過,難免是在熱興頭上潑冷水。我希望你打過冷顫之後,可以抖擻精神,重新做一番有價值的事業。
最佳賣點 : 朱光潛看重詩:「要養成純正的文學趣味,最好從詩入手。能欣賞詩,自然能欣賞小說、戲劇等文學種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