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馬依北風
| 作者 | 席慕蓉 |
|---|---|
| 出版社 | 叩應股份有限公司 |
| 商品描述 | 胡馬依北風:我可以這樣說嗎?在這條創作的長路上,自己一直是個心懷感激的寫生者,以親身的感受和行走作為基礎。是的,是生命在激發我,而我怎樣也不捨得忘記……如此而已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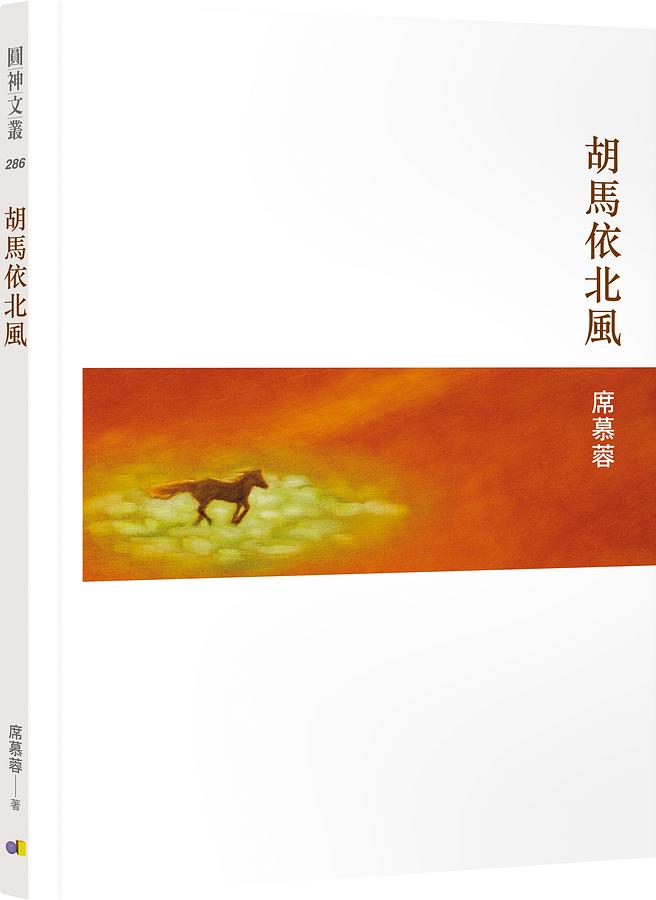
| 作者 | 席慕蓉 |
|---|---|
| 出版社 | 叩應股份有限公司 |
| 商品描述 | 胡馬依北風:我可以這樣說嗎?在這條創作的長路上,自己一直是個心懷感激的寫生者,以親身的感受和行走作為基礎。是的,是生命在激發我,而我怎樣也不捨得忘記……如此而已 |
內容簡介 我可以這樣說嗎? 在這條創作的長路上,自己一直是個心懷感激的寫生者, 以親身的感受和行走作為基礎。 是的,是生命在激發我, 而我怎樣也不捨得忘記……如此而已。 三十年前,《信物》以荷花為題,書寫創作;三十年後,席慕蓉以游牧文化為題,回首凝望。 三十年的時間就在行走和追索探問之間慢慢地過去,曾痴心描摹的蓮荷,一夕之間對象轉為馬與原鄉。創作的描述不同,但本質沒有絲毫改變,都是生命的見證。 越過光陰長河,《胡馬依北風》除了見證創作長路迢遙,並同時紀念著創作者與出版社之間合作三十年的美好時光,依舊波光粼粼。
作者介紹 席慕蓉祖籍蒙古,生於四川,童年在香港度過,成長於台灣。於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系畢業後,赴歐深造。一九六六年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於比利時布魯塞爾皇家藝術學院。在國內外舉行個展多次,曾獲比利時皇家金牌獎、布魯塞爾市政府金牌獎、歐洲美協兩項銅牌獎、金鼎獎最佳作詞及中興文藝獎章新詩獎等。擔任台灣新竹師範學院教授多年,現為專業畫家。著作有詩集、散文集、畫冊及選本等六十餘種,讀者遍及海內外。近二十年來,潛心探索蒙古文化,以原鄉為創作主題。現為內蒙古大學、寧夏大學、南開大學、呼倫貝爾學院、呼和浩特民族學院等校的名譽(或客座)教授,內蒙古博物院特聘研究員,鄂溫克族及鄂倫春族的榮譽公民。詩作被譯為多國文字,在蒙古國、美國、日本及義大利均有單行本出版發行。席慕蓉官網:www.booklife.com.tw hsi-muren.asp
產品目錄 代序:長路迢遙 海馬迴 輾轉的陳述 記憶或將留存 普氏野馬 溜圓白駿 後記:如此厚賜 附錄:出版書目
| 書名 / | 胡馬依北風 |
|---|---|
| 作者 / | 席慕蓉 |
| 簡介 / | 胡馬依北風:我可以這樣說嗎?在這條創作的長路上,自己一直是個心懷感激的寫生者,以親身的感受和行走作為基礎。是的,是生命在激發我,而我怎樣也不捨得忘記……如此而已 |
| 出版社 / | 叩應股份有限公司 |
| ISBN13 / | 9789861337333 |
| ISBN10 / | 9861337334 |
| EAN / | 9789861337333 |
| 誠品26碼 / | 2681940409009 |
| 頁數 / | 120 |
| 注音版 / | 否 |
| 裝訂 / | P:平裝 |
| 語言 / | 1:中文 繁體 |
| 尺寸 / | 23X17X0.9CM |
| 級別 / | N:無 |
最佳賣點 : ◆ 從蓮荷到駿馬,三十年創作長路迢遙,這本書是生命的見證,更是一位作家與出版社共同銘刻,慶賀深厚情誼的芬芳信物。
自序 : 後記:如此厚賜
在二○○五年四月十一日的日記裡,曾記下和齊邦媛老師的一段對話:
「今天近中午時分,和齊老師通了一次電話,老師剛好在臺北家中,談興很高。這之間她引用了一句英詩,大意是:
「現在的我只想在路邊坐下
細細地 回想我的一生。」
齊老師當時曾說了詩人的名字,但我沒記住。只是非常喜歡這句詩,就在晚上寫日記的時候,把這種感覺記下來。
原來,一句詩,可以如此具象地呈現了創作源頭的那種渴望。原來,從很幼小的時候開始,我就是自己的旁觀者。遇見不捨得忘記的時刻,就會叮囑再三:「不要忘記,不要忘記!」於是,在成長的過程中,就常常喜歡在路邊或者桌前坐下,以畫面與文字,來細細回想剛才經過的一切……
但是,怎麼會那麼剛好?
在我生命中最重要的那個關鍵時刻裡,前前後後,圓神出版社竟然幫我出版了四本書,作為最精確的見證:
一九八八年三月出版的《在那遙遠的地方》,是住在香港的攝影家林東生先生經由曉風的介紹,自告奮勇在一九八七年夏季,以四十天的時間去內蒙古為我尋找並拍攝我父親故鄉附近的景象,再加上我曾經寫下的與自己鄉愁有關的散文,合成一冊,由圓神出版。
那時的我,並沒有察覺到周遭也在變化。是的,僅僅是一年多的時間之後,自出生到四十多歲都被隔絕在外的我,這個遠離原鄉的蒙古女子,竟然可以親自前去探訪了!
一九八九年八月底,我站在父親的草原上,是整整前半生總是遙不可及的大地啊!如今卻就在我的眼前,我的腳下,等著我,等著我開始一步一步地走過去……
雖然只有十幾天的行程,只去探看了父親的草原和母親的河。但是,那奔湧前來的強烈觸動如眼前的草原一樣無邊無際,如身旁的河流一樣不肯止息;於是,一九九○年七月,《我的家在高原上》出版了。除了我的文字之外,還有同行好友王行恭為我拍攝的更多的極為難得的現場畫面,並且還由他擔任美術編輯的工作。
怎麼會那麼剛好?這封面一綠一紅的兩本書,《在那遙遠的地方》和《我的家在高原上》見證的,是在短短一年多的時間裡,因為世事的突變,身為當局者的我所生發的百感交集……而也由於這兩本書,我終於可以得到了臺灣朋友的同情,以及,蒙古高原上的族人的接納。這樣的情節如果寫在小說裡,讀者一定會認為太過牽強。可是,在真實的世界裡一切就是如此,有書為證,感謝圓神。
現在再來說另外兩本書,《信物》與《胡馬依北風》吧。
《信物》一書,出版於一九八九年一月,其實還早於我的還鄉,是在圓神出版的第二本書。
我想,從一九八八年第一本《在那遙遠的地方》合作開始,簡志忠社長和我這個作者之間,就有了一種「默契」。是的,在這裡,出版者和作者都還保有一些比較天真的願望。我們兩人都經歷過困苦的童年和少年時期,許多累積著的對「美」的想望,總是在被壓制或者被勸誡的狀態下,難以成形。 可是,生命本身有些質素卻極為頑強,一有可能,它們就萌發、成長。這本《信物》,或許就是出版者和作者共同的心願,以表達出自身長久以來對單純的「美」的想望吧。
這本《信物》,在當時的臺灣可以說是少見又有些奢侈的新書。精裝本全球限量兩百五十冊,由作者親自編號、簽名,並且還附贈一張以版畫方式精印的藏書票。
書的主題是蓮荷。文字只有一篇六千多字的散文,敘述我多年以來傾心於描寫蓮荷這種植物的起因,以及,種種與此有關的學習和創作過程的心情。貫穿全書的則是我在前一年(1988)夏天,剛好獨自一人遠赴峇里島上的小鎮霧布,在當地的荷池旁,以兩個星期的時間寫生而成的素描,大大小小共有二十多張。是清晨速寫回來之後,整個下午,再在旅舍房間的露臺上,重新以針筆和水彩筆構成的單色素描。
以下是書中的一段文字:
……住在我對面,隔著一大叢花樹,有時候只聽其聲不見其人的是一對德國夫婦,大概注意我很久了。終於有一天,在院子裡互道了日安和交換了天氣出奇的好之類的寒喧之後,金髮嬌小的妻子忍不住問我,是不是在寫小說?
我笑著否認了,並且邀她到我屋前的平臺上來,給她看我的速寫和素描,告訴她說,我是來這裡畫荷花的。
她轉過身來興奮地向她的丈夫說:
「你聽過這樣的事嗎?一個人跑到這麼遠的島上來只是為了畫一朵荷花?」
她這句話說出來之後,我好像才忽然間從別人的眼睛裡看到我自己,原來是這樣的荒謬而又奢侈——
整整一個夏天,只為了畫一朵荷。
可是,整個事情,果真是像它表面所顯示的那樣嗎?我回來了之後,一直在想這個問題。
荒謬的意思就是不合理,奢侈的意思就是浪費。可是,要怎樣的生活方式才能是合理而又不浪費的呢? 我們的生命,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命,不都是一件奢侈品嗎?
要怎樣用它,才能算是不浪費呢?
這些是一九八八年深秋之後,寫在《信物》裡的一段文字。其實,前一年在峇里島上速寫蓮荷之時,並沒預想到這些畫作會單獨成為一冊精裝限量版本的主題。而等到一九八九年一月書成之時,和朋友們歡喜慶祝的時候,也完全不能預知,還有更歡喜和更奢侈的道路就在不遠的前方。
是的,僅僅只在《信物》書成的幾個月之後,我就從前半生這小小安靜的世界裡突然跨入蒙古高原那時空浩瀚的故土之上了。
三十年的時間就在行走和追索探問之間慢慢地過去……
今天,正在為《胡馬依北風》這本新書寫後記的我,身在二十世紀第二十年的盛夏,端午剛過兩天。前幾日才知道簡志忠社長還是堅持要再出版一本限量版的精裝新書,以紀念和慶賀我們合作三十年的美好時光。
真的啊!怎麼可能一合作就是歡歡喜喜的三十年了呢?
這一次,新書所有的稿件都已齊備,只差我筆下的這篇後記。
新書的主要內容是兩篇散文中的三匹蒙古馬,再加上幾幅我畫的與原鄉有關的畫作,書名是《胡馬依北風》。
感謝圓神,怎麼會那樣剛好?前面有兩本相距只有兩年時間的書,為我留下歸返原鄉之前《在那遙遠的地方》的萬般惆悵,和《我的家在高原上》初見原鄉時的狂喜和憂傷,甚至還有憤怒……
那曾經坐在路邊細細回想的一切,圓神都讓它成書,成為生命的見證。
而今天,兩本相隔超過三十年的《信物》與《胡馬依北風》所要見證的,卻幾乎是比三十年更為加倍長久的時光裡,我在稱為「創作」這條長路上的變與不變了。
在《信物》中以二十多年的痴心去描摹的蓮荷,可以在之後的一夕之間棄而不顧,這變動從表面上看來不可說不大。
而在三十年後的《胡馬依北風》裡,除了描摹和敘述的對象改變了以外,那無論是時間上的深遠和空間裡的巨大都是無可否認的改變。
但是,我可不可以這樣說?是生命在激發這些變化,而我創作的本質依然沒有絲毫改變。
我可以這樣說嗎?在這條創作的馬路上,自己一直是個心懷感激的寫生者,以親身的感受和行走作為基礎。是的,是生命在激發我,而我怎樣也不捨得忘記……如此而已。
三十年來在圓神出版的書目,會放在這本新書的後頁。而三十年裡,能有這樣的四本書作為創作初心的見證,是簡志忠社長,以及所有工作伙伴給我的厚賜。
在圓神的美編團隊裡,早先是和正弦合作,這幾年則是和鳳剛一起工作。兩人的風格不同,卻都是才情充沛的年輕人,有好幾本詩集的封面都各有特色。我尤其喜歡散文集《寧靜的巨大》封面的感覺。在工作中,他們好像也能寬諒我的猶疑不決,知道我正在一個新的世紀裡努力去學習和適應呢。
最知道我的這種掙扎的是近幾年的主編靜怡。在電話裡,她的聲音總是平和舒緩。可是,在討論的時候,她卻常常會激發出我對創作的熱情而快樂起來,很溫暖的感覺,好像剛才曾經面對的困難已經不再是困難了。
想一想,在這超過三十年的時光裡,無論是畫一本荷或者敘述三匹馬,整個出版社都來給你護持和加持,卻從來沒給你任何壓力,總是任由你安靜而又緩慢地繼續寫下去,這是多麼難得的情誼啊!
如此厚賜,我深深感激。
內文 : 記憶或將留存
馬的馴化,是在新石器時代晚期,所以,此時的岩畫裡,馬是無處不在的。感謝這些卓越又真摯的初民,他們是以詩以畫來作為一個記錄者,為自己、為族群,也為後來的人,將記憶慎重保存。
游牧文化最早的線索都深藏其中,有幾幅出獵圖的繁複和生猛真的是嘆為觀止啊!
當然,在生物演化史上,馬來得比人類早得多了。聽說,最早的馬體形極小,學者稱牠為始祖馬(Hyracotherium),出現在大約是五千六百萬年之前的始新世早期。又有個好聽的名字叫朝馬(Dawn Horse),是黎明時分的象徵嗎?這樣的名字幾乎可以拿來寫一首詩了。
然後是漸新馬(Mesohippus)、草原古馬(Merychippus)、上新馬(Pliohippus)等等。經過這些主要的演化階段之後,才逐漸發展為此刻的真馬(Equus)。
不過,學者又說,「發展」這個詞語容易引起誤會,以為馬的演化是越來越擴大的狀況,其實剛剛相反,馬的演化是難以了解的趨向凋零。曾經有過枝繁葉茂的美好時期,最鼎盛之時,曾經多達十三個屬的蓬勃多樣,如今卻都消失到只剩下真馬這孤單的一個屬了。
所以,我們現在是這樣把牠歸類的,牠是在哺乳動物綱,奇蹄目之下的真馬屬。這裡面包括了普氏野馬、非洲野驢、亞洲野驢、山斑馬、平原斑馬和細紋斑馬等六個野生種,另外還有兩種家養類型,就是家馬和家驢。
而我們的蒙古馬就是由普氏野馬(其實原本就是準噶爾盆地上的蒙古野馬)傳延下來的。雖說已經馴化成為家馬,蒙古的牧馬人卻依舊在平日任由牠們在山野之間群居,主要是尊重並且希望能保持牠們的野性。這樣首先是馬的家庭制度不受影響,而且能繼續維護牠們自身對優生學的堅持。
馬是智慧極高的生物,在自己的家族裡堅持近親絕不通婚的原則。馬的情感也極為豐沛,即使長大後離開原生家庭,卻終生都戀念並且記掛著自己的父母和兄弟姊妹,同時對於照顧自己成長的主人也有著很深的感情。當然,牠並非天生就會聽命於人類,這馴化的過程是複雜而且緩慢的。大體上來說,馴化的工作從新石器時代的後期就已經開始,到了此刻,即使已經成為家馬,馬群中還是可能有從來沒被主人騎過的生馬,性格偏向半野生狀態,不容人類輕易靠近,所以,只有特別高明的騎手才能勝任。在內蒙古,一般稱這些馬匹為「生格子馬」,要馴服牠是漸進的「感化」過程,通常需要至少一個月左右的時間。這感化,是真正的以愛與關懷的感情化育。除了剛開始是不得不用強制性的手段之外,牧馬人從來不用鞭子加諸馬身,而是以尊重甚至讚嘆牠的不屈的野性讓這匹駿馬不覺得是受到凌辱,並且終於了解主人想要與牠接近的心意。
是的,馬的智慧足以讓牠明白自身的價值。而在蒙古草原上長大的牧馬人,他馴服一匹馬的本意也絕非只是想要以暴力來駕御一個終生只好任他驅使的工具和奴隸。不是這樣的。一個蒙古牧馬人,他真正想求得的是一位可以信任的工作伙伴,一個可以一起往前路馳騁的朋友和知已,甚至最後情同最親的家人。
在蒙古高原上,一匹馬和一個蒙古人之間生死以之的美好情緣是說也說不完的。無論這匹馬是戰馬而牠的主人是身經百戰的英雄,或者這匹馬是老馬而牠的主人只是一個卑微的醉漢。在長篇的史詩或者短短的民間故事集裡,在如海洋般匯集的長調或者歌謠裡,這些珍貴的記憶都被反覆書寫、吟誦以及高歌,然後再成為一代又一代綿延下去的無可取代的文化素材……
二○一三年十二月八日的下午,在臺北熱鬧的市中心,我曾經心無二用地靜靜聆聽一位新疆的錫伯族學者解說在兩百多年之前(一七六四年)被清廷從東部科爾沁蒙古的原居地抽調到新疆去戌邊的錫伯族人長途跋涉的經過。其間,我忍不住問了一個問題:「一個民族的記憶要如何傳遞下去?」
他的回答出乎我意料的極美。
他說:「所有的歌謠裡都有記憶。」
現在,在這篇文字的最後,我想轉述一位蒙古女子珍存了半生的一段記憶。或許許多年之後會有人將它寫成一首詩,再有人將它譜成一曲歌謠。不過在此刻,這段記憶只在她流下的淚水中顯現……
那天是二○一八年九月九日的下午,在呼和浩特市郊一場熱鬧的聚會裡。是朋友好心,知道我正在寫一本關於蒙古馬的書,渴切地希望能夠再多知道一些知識和故事甚至傳說。所以他就邀請了好幾位從草原上前來的朋友與我見面。大家已經歡歡喜喜地告訴了我許多我聞所未聞的好材料,有人朗誦了一首詩,還當場幫我譯寫成漢文,有人說起古老的掌故和神話之間的關聯,有人唱完一首歌之後,再向我講述歌詞的大意和時代背景等等等等,我都興奮而又感激地記下了……
她就坐在我的正對面,始終安靜地微笑著聆聽這一切。她雖然有了點年紀,髮絲上已有了一層薄薄的霜雪,但姿容端莊,儀態從容,那秀異優雅的天生氣質,讓我這正在興奮狀態裡因而聲量特大的人也被懾服,終於安靜了下來。然後,隔著一張桌面的距離,我們兩人才開始互相凝視,並且微笑。先前朋友已經介紹過了,她是一位退休的行政人員。這時,我心想:「她會有什麼可以告訴我的故事嗎?」
我覺得她好像聽見我心裡的想法了。於是開始說話,依然是很輕,很文靜的聲音:
「我已經退休很久了。其實我的工作也和馬群沒有什麼關聯。但是,我年輕的時候,也曾經是『青年下鄉』浪潮裡的一分子。剛去到草原上的時候,我什麼也不知道,什麼也不熟悉。要我去放羊,我就去了。
當地的組織給了我一匹馬,應該那毛色算是雲青馬吧,當我的坐騎,陪我放羊。
牠還真是在『陪』我放羊呢。那時候在草原上,遠離都市,還真是沒有什麼人來管我,沒有什麼特別的規定或者嚴格的要求。我每天早出晚歸,唯一要做到的事,就是放好那一群羊。開始的時候我還有點害怕,因為不知道要如何照看。等到逐漸進入情況之後,只要羊群聽話,我自己的時間就越來越多了。我會帶一本書在樹底下慢慢地翻看,而那匹雲青馬就在不遠的地方走動,也不離開。
逐漸地,我注意到怎麼好像是牠在替我看管羊群。有那調皮的羊羔子走散了的時候,是牠去把牠們趕回來。那時草原上偶爾還有狼,還不等牠們接近,這匹雲青馬早早聞到牠們的氣味,就會向我嘶叫示警。只要我站起來發出驅趕的聲響,狼是怕人的,也就跑了。
慕蓉老師,您要知道,那個時候的我也不過是個十八、九歲的孩子。一個人離開了父母,從老遠老遠的城市來到草原,真可說是舉目無親的孤單啊。雖說有草原上的老額吉(母親)對我很照顧,可是心裡還是很苦悶。幸好有這匹雲青馬的陪伴,牠既像是我的朋友,又像是我的兄長一樣,好像雖是我在放羊,牠的任務卻是要負責照看好這個正在放羊的我。
那一段時間裡,我雖然明白這一切都是很難得的,可是還沒把這些真正當作一回事,只是每天這麼平平順順地過著而已。
後來,大飢荒來了,日子越過越緊。當地的組織說另外有更重要的任務要調動馬匹,就把我的雲青馬要回去了。牠走的時候匆匆忙忙,我連抱牠一下向牠道別的機會都沒有,就這麼分開了,也是無可奈何吧。
那次的災情持續了很長一段日子,我們非常努力地想盡了所有的辦法讓自己和大伙兒都可以活下來。有時腦子裡會閃過一些念頭,猜測雲青馬現在在什麼地方?可是,坦白說,如此疲累的日子,連想念一匹馬的念頭都是太奢侈的事,還有許多工作要打起精神來面對呢。
沒想到的是,有天晚上,雲青馬竟然跑回來找我了。我還住在原來的地方,聽見牠用前蹄刨地,輕輕地低聲嘶鳴,那麼熟悉的聲音啊!我急著跑出去,真的是牠,是牠回來看我了!
那天晚上有一點月光,讓我能夠看出來牠有點瘦了,不過身體整個狀況好像還可以。牠的眼睛依然有神采,一直向我望過來,是我的雲青馬啊!我心裡疼惜得不得了,就想進屋去拿點東西來餵牠。可是我也知道,今天晚上屋子裡什麼糧食都沒有,就只有一小把剩下來的黑豆。
我急急地跑進屋去拿了那把黑豆出來,走近我的雲青馬,用兩手掌心併攏,托著那一把黑豆,放在牠的唇前,向牠說:
『對不起,我只剩下這些了。你把它們都吃了,好嗎?』
牠低頭靜靜把我手掌心的黑豆吃了,那柔軟又溫暖的唇和舌,彷彿在接觸我的掌心之時,也把一股暖流送到我的全身。這麼久的時間裡,無論多麼辛苦都沒有流過一滴淚的我,這個時候像觸了電一樣,淚水撲簌簌地止不住的往下落,也不敢出聲,怕驚動了別人。
這個時候,雲青馬也不出聲,牠只是把牠的頭偏向我,輕輕靠近我的面龐和脖頸,用一匹馬所能表達的最慎重的愛意,陪著我靜靜地站在一起。
那時間也許很長,也許只有片刻,我當時已經無法分辨。因為,最後,牠還是離開我,走了,並且從此沒有再回來。
我和牠都知道,我們那時是必須要分開的。所以牠走的時候並沒有回頭,我也沒再跑上去跟著牠再走上一段路。牠能再回來看望我,當時對我已是極大的安慰和幸福,唯一的遺憾是我只有那麼那麼少的一小把黑豆……
慕蓉老師,這麼多年都過去了,我一直很想念牠,一直忘不了牠。忘不了牠在微微的月光下慢慢走遠了的背影,我真想牠。」
坐在我對面秀麗的蒙古女子停止了她的敘述,淚珠仍在她的眼角閃耀。我本是無言以對地靜靜凝視著她,但是突然有一句話自己越過了我的一切思維向她說出來了:
「就是因為妳對牠的想念,才把牠留在這個世界上,沒有離開。牠一直在妳的想念裡活著,就是活著。妳看妳現在告訴了我們,我們也都覺得牠還是活著的啊!」
這句話不是我想到的。可是,說出來之後,我發現對面的她聽進去了,並且在瞬間向我展現出極為欣慰的笑容。親愛的朋友,妳可知道,這句話,在同時也是對我的昭示。原來,我和妳一樣,也是在突然間明白了一些什麼……
原來,這人世間的悲喜遭逢是由不得我們來選擇的。可是,憑藉著自身那誠摯的愛和想念,卻絕對可以將我們最珍惜的記憶留存。
審慎留存在詩裡、畫裡、歌裡、在你一個人默默的想念裡。無論經過多長久的時間,只要一動念,一迴身,昨日便翩然而至,而妳的雲青馬在月光下,完好如初,並且永遠不離不變……
是的,我是這樣相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