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獨課
| 作者 | 亞然 |
|---|---|
| 出版社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 商品描述 | 孤獨課:為什麼留學?為什麼浪遊? 他所選擇的,其實是一種精神生活方式。 完美融會冷靜與熱情的篇章,記錄了青年亞然求知若渴的「純真年代」 亞然,90後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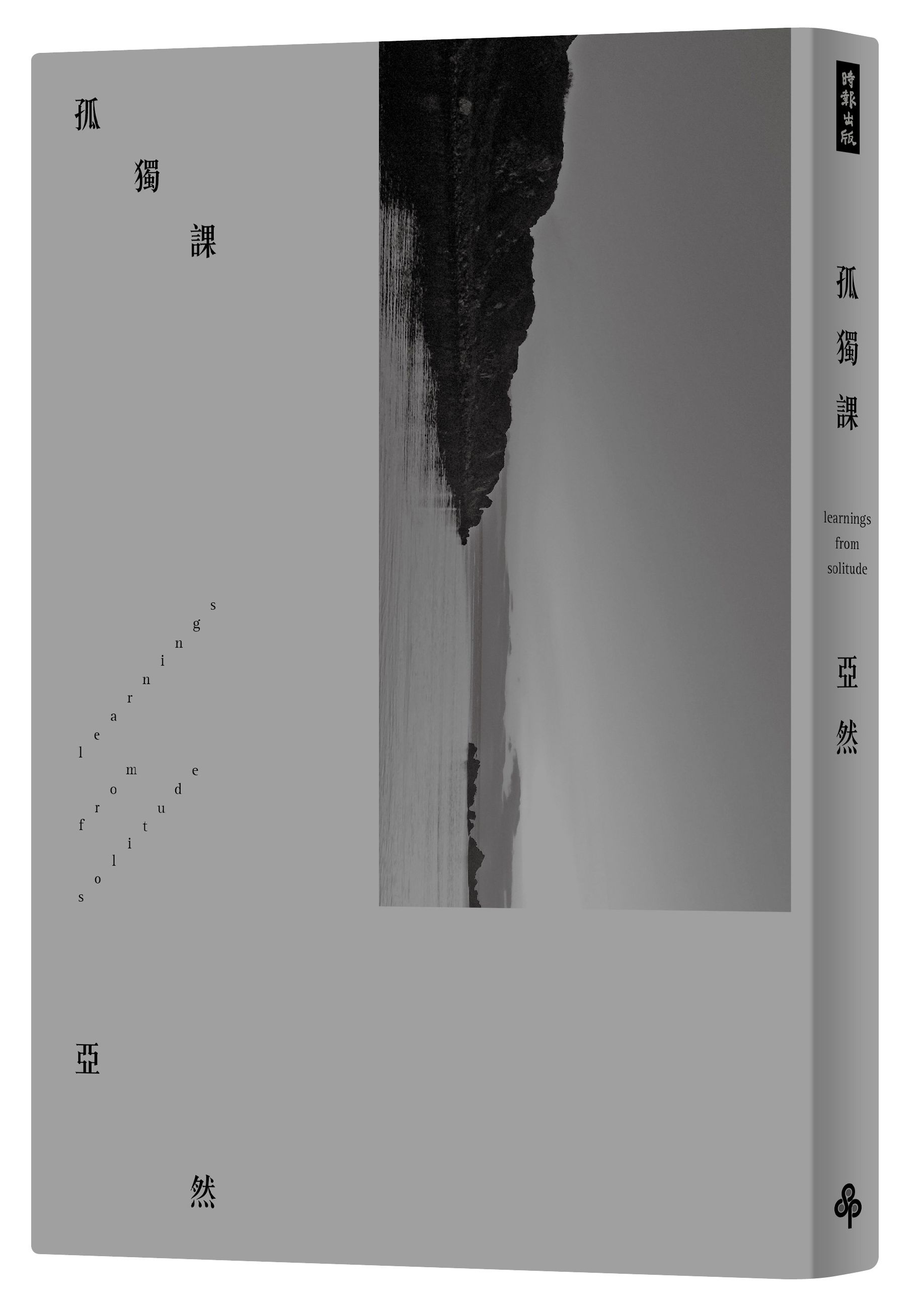
| 作者 | 亞然 |
|---|---|
| 出版社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 商品描述 | 孤獨課:為什麼留學?為什麼浪遊? 他所選擇的,其實是一種精神生活方式。 完美融會冷靜與熱情的篇章,記錄了青年亞然求知若渴的「純真年代」 亞然,90後 |
內容簡介 為什麼留學?為什麼浪遊?所選擇的,其實是一種精神生活方式。文字完美融會冷靜與熱情,記錄了青年亞然求知若渴的「純真年代」亞然,90後出生的香港新銳作家,他是馬家輝的忘年文友,受到陳冠中啟發而開始寫作,二十來歲,卻已經歷了留學英、德、專攻歐亞史,並曾在台灣居住做研究。他不但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同時也十分懂得旅行與生活,品評起音樂、足球、威士忌,頭頭是道。《孤獨課》,就是這麼是一本關於留學生活以及歐亞洲不同社會文化觀察的散文集。一個香港人到英國讀書,到台灣研究寶島政治,來回三地漂泊生活。研究生的生活枯燥而孤獨,所以在讀書路上不應該也不能夠只有讀書、或只讀有關研究的書。這幾年在異地生活,時間都在圖書館、音樂廳,或在球場、書店、酒館中度過,而這本書的文章就是記下在這些地方所遇到的人和事。身為一個學養淵博的青年學者,他事事上心,音樂、美食、旅遊皆生動入篇,敏銳捕捉不同城市中迷人的故事日常。在倫敦音樂廳聽到蕭斯塔高維契的音樂,會想到在這個歐洲城市跟俄國十月革命的密切關係;在蘇格蘭的小島欣賞威士忌之餘,更欣賞在小島上生活的人所營造社區關係;在台灣吃牛肉麵,又會吃出餐館背後一個家庭的結合和別離。作者雖然年輕,文字卻沉穩而理路清晰,對知識的渴求,對正義真理的追求,這些博學多聞、融會冷靜與熱情的篇章,記錄了他的「純真年代」,讓讀者看見並伴隨他的精神浪蕩。正如馬家輝所讚賞:「一代連一代的讀書人的精神生活,確是常用這樣的方式記錄和傳承下來的。而讀書人,其實從來不曾孤獨過。」
各界推薦 ◎聯合推薦(依姓氏筆畫順序排列)馬家輝陳冠中張鐵志「《孤獨課》正是一位年輕讀書人的精神生活方式的文字記錄。過去幾年,關仲然處於外地留學的遊走狀態,知識是他的核心養分,並由此衍生枝葉,透過書寫,在不同的香港媒體上向他的同輩讀者展露容顏。」--馬家輝「亞然現在也是同時從事媒體書寫和學術研究。他可以兩者兼顧,並讓兩者彼此互補:在學術研究中融入現實的感受,在隨筆雜文中放入知識的魅力。這也是本書的清新與迷人之處。」--張鐵志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亞然本名關仲然,1993年生於香港,香港新一代文化人、專欄作家。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畢業,現為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博士候選人、德國杜賓根大學歐洲當代台灣研究中心短期學者。研究香港及台灣政治,專研選舉、政黨及社會運動。 除政治之外,興趣涉獵甚廣,對音樂、足球、威士忌都有研究。專欄見於香港《明報》、BBC中文等,同時為學術期刊、包括《中國季刊》(China Quarterly)等撰寫書評。
產品目錄 推薦序:那一年的旁聽生/馬家輝推薦序:重回對這個世界的初衷/張鐵志自序:緣起:踏上讀書這條路I 讀書的路途孤島大留學潮在倫敦的半年漂泊生活熟悉的建豐二年左翼重鎮--亞非學院是傳記抑或傳奇倒數中的古巴像王強一樣的書蠹從台北書展到台灣研究百花里族人讀博士的困難討厭考試愛書人天堂錯過了的時代讀書有用研究生完全求生秘訣蝦湯拉麵和雞湯拉麵不是雪泥鴻爪II 生活的乾澀和快樂人一旦愛,遂極脆弱不會脫節倫敦很危險文化差異拯救了我的聖誕燈飾文化沙龍上癮之必要倫敦指南食在倫敦三個錦囊暫別英倫北上蘇格蘭避走日本聽風的歌電視節目有好多種香港小姐台式世界盃一個時代的終結:再見雲加夢碎與幻滅做個台灣人溫柔的台灣不太歐洲的蘇黎世廖家牛肉麵職人叉燒哪裏還有奧威爾的腳毛100%艾雷島威士忌盛世小王子III 我的comfort zone--音樂倫敦的夏天等我回來音樂會的最佳座位瘋狂指揮卡拉揚面對恐襲將世界變好一點學不到的斷捨離相約在音樂廳的頂樓皇家阿爾伯特地獄沒有永遠標準波坦金戰艦革命在倫敦在主教堂聽馬勒花甲之年不入樂廳,怎知動聽如此音樂政治家戴上指環的梵志登行人地獄最後一夜敦克爾克IV 政治2016危險的一年可惡的三月有選舉就好鄰舍與仇敵把荒謬留給電視劇從廢墟中復活只能相信百年之後這一個晚上智慧城市與自慰城市恐怖的大台恐襲與恐懼圖亭最有型毛澤大道東與轉型正義沒得救了第一步可惜我聽不懂【後記】
| 書名 / | 孤獨課 |
|---|---|
| 作者 / | 亞然 |
| 簡介 / | 孤獨課:為什麼留學?為什麼浪遊? 他所選擇的,其實是一種精神生活方式。 完美融會冷靜與熱情的篇章,記錄了青年亞然求知若渴的「純真年代」 亞然,90後 |
| 出版社 /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 ISBN13 / | 9789571377490 |
| ISBN10 / | 957137749X |
| EAN / | 9789571377490 |
| 誠品26碼 / | 2681731854001 |
| 頁數 / | 288 |
| 開數 / | 25K |
| 注音版 / | 否 |
| 裝訂 / | P:平裝 |
| 語言 / | 1:中文 繁體 |
| 級別 / | N:無 |
自序 : 【自序】
緣起:踏上讀書這條路
關於這本書、關於自己,大概要從如何踏上讀書這條路開始說起。
中五會考之後(我是末代會考生),等待放榜的幾個月百無聊賴,誤打誤撞在書店買了陳冠中的小說《盛世》來讀(說是誤打誤撞,因為以前走入書店,大概都是跟家人進來,自己走去看文具玩具打發時間,看書從來都是其次),認真一讀之後,發現讀書原來如此有趣。
你可能會問,為什麼是《盛世》?為什麼是中五之後?我只能說,啟蒙就是這樣一個過程,很隨機、很spontaneous。讀完《盛世》之後,立刻再找陳冠中的其他書來看,然後讀又慢慢讀其他的作者,像董橋、像馬家輝、像梁文道等等,都是精彩的散文、鏗鏘的評論,就這樣不經意的打開了讀書之門。現在回看,我的讀書之門的開啟是非常的「本土化」,都是從香港作家開始。
我的興趣和方向,都是靠着讀書而慢慢摸索出來。讀書就是這樣一回事,每讀一本書,總會令你知道下一本應該讀什麼書,一發不可收拾。所以,如果《盛世》是一個開始的話,那麼當時對我最重要的一本書,就是周保松教授的《相遇》。我是讀了《相遇》之後,才讓我以進入中文大學政政系為目標。周生所寫的是對政治、對社會,以至對人生的思考,都是我讀大學以前沒有想過的事。愈是有所思考,愈需要通過閱讀來補充思想上的缺乏。畢竟過去在中學的時候,選了以為是「更有型」的理科、日常進出的是實驗室而不是圖書館,除了勉強死記硬背過一些化學元素和方程式外,腦入面幾乎一片空洞。
喜歡閱讀不一定喜歡寫作,但喜歡寫作的很難不喜歡閱讀,否則沒有半點墨水,想寫也寫不出來。我走上寫作的路、將思想感受訴諸文字其實比開始閱讀來得更無厘頭。中學時候討厭作文,無論是考試抑或功課,作文不及格都經常發生。但從小到大,都聽過父親說報紙有「投稿」這回事,因為他常常都說很久以前曾經投過稿也刊登過,這是一件「威水事」。
然後在17歲、就讀中六的時候,發生了「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趙連海的兒子是受害人,爸爸提出申訴反而遭判監。放學回家的時候在火車上看到相關新聞報導,那時還年輕,覺得世界豈能如此不公,心裏有種書寫之必要,所以回家之後立即坐在電腦前面,草草寫了一篇五百字的短文,然後投稿給《明報》副刊的「自由談」。寫完寄出之後一直沒有任何音訊,那時候我也沒有每天追讀副刊專欄,所以就此作罷,反正是那一刻覺得義憤填膺,不吐不快,既然吐完也就算了。
就這樣過了大概半年之後,無端端收到編輯電郵,向我索取個人資料,原來文章很久以前就刊登了、要發稿費給我,那時候我還未成年,連銀行戶口也沒有開。當收到稿費之後、發現自己所寫的文字原來可以刊在報紙上,從作文不及格到可以在報紙上寫東西,寫作忽然之間為我帶來很大的成功感。自此以後開始不斷寫作,也從寫作之中得到很大的喜悅。雖然那時候寫的文字,現在看起來是絕對的不堪入目,但感激那時候的編輯,他們的一個決定改變了我很多。
回到讀書,在閱讀過程中,很多我所喜歡的作家都會寫他們年輕時在外地或生活、或留學中的人與事,像董橋、李歐梵、周保松、馬家輝、雷競璇等等等等,他們都貫徹了一代又一代留學生書寫留學生活的傳統,這些「留學文學」的文字都打動着我。
我想,即使年代已經不同,我也想過一次像他們筆下的留學生活,然後把自己的留學生活記錄下來。最後我來到英國留學,選了在亞非學院讀研究院,在書店在球場在酒館、在圖書館在音樂廳,渡過了很多個白晝和夜晚。這本書的文字,也是寫在這些地方所遇到的人與事。
離鄉別井身在異地,英文是diaspora,這個英文字總是帶點無以名狀的滄桑感覺。獨個兒在外地生活,永遠都有一種近乎沒有規範的自由,因為你不是本地人,無論你如何打破語言的界限、怎樣融入當地的生活之中,你始終都會跟那個不屬於你的城市保持着一種距離。但這種距離不必然是負面的情緒,反而是通過這種自己與所住的城市之間的距離、自己與我城香港的距離,可以保持一種清醒,得到有很多空間去思考。而這本書的文章,就是以diaspora的視角,記下在留學生活中所遇到的人與事。
書分成六個主題,寫讀書、寫生活,也寫政治、音樂和人物。因為都是人在留學讀書的時候書寫,所以歸根結底,「讀書」是貫穿全書的重要主題,或者應該說,我的身份本來就是讀書人,所踏上的也是讀書這條路。文章是近兩年所寫,主要寫在倫敦,也有一部份在台北和香港書寫。
因為踏上讀書這條路,所以才會打開一道又一道的門。這段路我只是剛剛開始走上,而這本小書是我讀書生活中的一點記載,也標誌着這個旅程的開始。
是為序。
導讀 : 孤島
讀書研究的生活必須規律,無論在倫敦抑或台北都一樣,都是起床、吃飯、工作、然後回家;聖誕也好佛誕也好,都跟我們沒有關係,因為研究生的日曆每一天都是黑色的:沒有假期、沒有休息。
做研究的生活規律之餘,而且孤獨,當台灣的麥當勞最近也可以自助點餐的時候,真的可以一天到晚完全不用開口說一句話。所以no man is an island這句說話其實不對,每個研究生其實都是一座寂寞的孤島。
難怪久不久就有報導說,要多多關注研究生的心理健康,最近美國有研究發現:研究生比一般人感到抑鬱焦慮的機會超出六倍。人的情緒就像一個循環,總會有固定時間的潮起潮落。我的專欄一直以來都寫讀書的生活,讀者或多或少應該捕捉得到我最近的情緒狀態處於什麼位置。
我在台北住古亭、工作的地方在大安,之前氣溫還在三十度以下,可以穿過大安森林公園慢慢走到辦公室,總見到一群大媽聚集晨運、幾隻松鼠跑來跑去,還有一對又一對的男女男男或女女在拍拖在親熱。但六月未到,台北已經熱得像火爐,看新聞說今年台灣香港都一樣,都是破紀錄的炎夏。一到室外已經全身濕透、幾乎立即溶掉,我差點以為自己是瑪利歐,去了會噴火有熔岩的世界。
因為只在台北待半年左右,可以租住選擇的地方都沒有太多,最後選了一間小小的劏房,就在一棟老舊的大廈裏面。房間樓底很高,台灣人說這些是「樓中樓」,床就在閣樓上面。對於常常在家工作的人來說,書枱跟床的距離還是愈遠愈好,分成兩層就最好不過。不過劏房沒有窗口,外面天晴抑或下雨都不知道;而且沒有廚房,一天三餐都要在外面解決,思考「晚餐吃什麼」就成為每日最大的難題。
讀書人容易覺得孤獨和失落,不過反過來也一樣容易快樂和滿足,到書店逛逛然後捧著一堆新書回家就是最好的方法。最近讀江勇振教授寫的《舍我其誰:胡適》(剛剛出到第四部)讀得入神,讀胡適先生如何走上留學的路、又如何從修讀農學轉到哲學。胡適是留學生,我也是留學生,就算永遠不可能成為胡適,也要以胡適先生作為目標,奮鬥一下。
最近還有一件小事為我的苦悶生活帶來一點歡樂。在台灣銷費,無論飲食玩樂都總有張發票(即單據),台灣人總會收集這些發票,為的是參加由政府舉辦、每兩個月一次的發票號碼大抽獎,特別大獎的獎金是1000萬新台幣。
去過我住處的朋友都笑我像獨居老人,因為我有個裝滿發票的信封。而且每晚回家之後,總會將當日的發票資料輸入手機的「雲端發票app」,方便「對獎」。最近終於開獎,在我一共百多張發票之中,有兩張中了「六獎」,共得400元正,真是可喜可賀,對嗎?
大留學潮
眨眼來了倫敦差不多三個月,開學之後一直大忙,讀了很多課程相關的書和文章,充實到不得了。因為忘我投入學海,很快就適應新生活。這裏的生活簡單,就是讀書和照顧以往不需自己照顧的三餐飲食,即買餸煮飯。機械一般的生活,日復一日,時間轉眼就過。
身邊大半的同學都來自不同國家,大家最常講的都是記掛自己老家,念茲在茲的都是家人和朋友、還有天氣和食物。我還記掛以前常常流連書店的日子,來回掃射「豬肉枱」上的變化,哪本書是新出版哪本書搬上架了,基本上都掌握一二。現在要在倫敦讀新出版的中文書,動輒要女友寄包裹飛越半個地球才能讀到,運費跟書價看齊(甚至更貴),實在太過奢侈,所以至今只寄過一本、讀過一本。寧願寫下書單,待回港之時才買過痛快。而那本越洋寄來的書,是和自己非常貼切的一本書——《大留學潮》。
貼切因為自己是個留學生,而今時今日也是千百年一遇的「留學大潮」。二月(2015年)的一期《經濟學人》,指在2013年尾,世界各地的中國留學生數目接近110萬,是史上最多。單計在美國就讀學士學位的中國留學生就超過11 萬人,非常嚇人。《大留學潮》的作者張倩儀(前商務印書館總編輯),寫的不是今時今日的留學大潮,而是寫那動盪到不得了的二十世紀初。單論人數,那時的留學生數目比現在少千百倍,但對中國的影響卻隨時大千萬倍。
現在的留學生,是為了求學求知識,說穿了是求一張「沙紙」;當年留學生想的卻是救國救民,希望學習別國之長、補中國之短。1905年科舉制的結束,標誌着海外留學潮的開始,書的其中一節「新科舉洋進士」,點出了留學生的精英地位,相當於科舉制下最高級的進士。清末民初的中國精英,第一等是出國的留學生(特別是得到公費資助留學的學生);而次一等的精英,就要數在國內大學讀書的學生。
兩種精英的其中一大分別,是學生的心態,而這又可見於內地大學的特色。中國第一代翻譯家嚴復的孫女、現在於加州帕克萊大學任教的學者葉文心,研究民國時期的大學。她所寫的《民國時期大學校園文化》就講了民初時期,不同院校的獨有文化。像聖約翰大學,是典型的精英西化學校,一般學生都不熱衷政治,讀課程主要關於英文訓練和科學學科。即使對社會事務較關心的復旦大學,後來亦因為經費問題,提供更多與職業訓練相關的課程,吸引更多學生報讀、增加學費收入。復旦將重心由社會學科主導改變為職業導向,犧牲的就是相對關心政治的傳統。
至於出國留學的精英,可以說是任重道遠。一方面學習現代化的知識,希望拯救陷於水深火熱的中國,從登上輪船開始已經滿腦子科學救國、實業救國等理想,他們就是打開長年封閉積弱的中國的一道鑰匙。無論這些留學生是否意會到這份責任,他們的一舉一動都影響外國人對中國的印象。
當時留學的難度,相比現在都困難得多,無論是飄洋的旅程抑或經濟狀况,跟今天的「留學」都不能同日而語。
今天坐十多個小時長途機已經覺得痛苦不堪,那時候要到歐洲,就要坐船經印度到非洲才能進入歐洲,頭暈嘔吐是肯定的。至於在外地生活,像打理家務、煮飯煲水,在當時中國男女性別定型之下的年代,處理這些家務不單單是「由零學起」,更要衝破心理障礙、突破男女之間的想像。就算是全國最精英的救國青年,都要做家務。
民國初年,中國國力疲弱得很,要出國留學談何容易。書中提到當年家境不俗的巴金,想要留學法國也幾乎要傾家蕩產,所以巴金的哥哥曾經勸他暫緩計劃,待家庭先儲點錢。但作為幼子的巴金堅持到法國,他哥哥也只能放棄前途、全力資助老弟留學。巴金去到法國之後,哥哥寫信問他外面世界究竟是如何,希望巴金分享一下。大哥為了成全老弟的理想而犧牲自己,這是兄弟之情,也是余華小說《兄弟》中的:「即使生離死別,我們還是兄弟」。
留學不容易,更遑論救國。不過如果我們不是將救國理解為那種「超級英雄式」的拯救世界,單單是出國留學、開開眼界,已經是踏出救國的第一步。像當年的其中一個留學熱點——法國,留學生對法國的最深印象,不是花都的浪漫,而是當地中小學對學生的管理。像寄宿學校中的嚴格作息時間、注重清潔衛生等,這種劃一的規律,對當時留學生來說是難以想像的。但一個國家要富強,良好的國民質素是首要條件。這也解釋了為什麼蔣介石的南京政府,為什麼在1920年代取得政權之後推出《新生活運動綱要》。這份綱要所要求的,就是衣食住行都要有規律,然後再談禮義廉恥。
大學生是浪漫的(前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說),留學生在外地應該更加浪漫。書中提到胡適先生在美國讀書時,他在1916年的時候,分別收到1210封信和寫了1040封信。即使今日科技發達,留學生也未必常常跟老家親人朋友聯絡,遑論書信,但胡適就平均一日寫近三封信。這千多封信中,又有多少是情書呢?
提到留學的浪漫,不得不談徐志摩,因為他跟劍橋的浪漫故事實在是個美麗的誤會。讀劉禾教授的《六個字母的解法》時,就有講到徐志摩的故事。首先,他在英國的時候不是劍橋大學的正式學生,他只是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的特別生,徐志摩在大部分的時間,甚至是住在距離劍橋頗遠的小鎮Saxton,所以徐志摩究竟在劍橋逗留過幾長的時間,都值得疑問。另一個誤會,是徐志摩推崇備至的康河,也一點都不浪漫。因為這條河是劍橋祼體協會的活動熱點。當徐志摩說「甘心做一條水草」的時候,其實同時有很多人在水草間祼泳,或許也是這個原因才令徐志摩如此「甘心」。
上一代國人的留學故事,其實都不是徐志摩的康橋故事。因為當時的時代背景,本身已經很困難。他們代表的中國,不是今天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強國,而是面對列強瓜分的中國;他們就算得到國家的公費資助,其實也只是國家打敗仗的庚子賠款,所以胡適才會說「留學者我國之大恥也」這句重話。這是上個世紀的留學歷史,也是今個世紀中國留學生所不能想像的歷史。
在倫敦的半年
V,帶來倫敦的那疊信紙,轉眼寫剩幾張,提醒我在這個跟香港很相似的城市已經生活了半年有多。離開香港之前,跟你許下承諾,要每個星期跟你寫一封信,除了交功課那幾個忙到發瘋的星期之外,我也守了諾言。對上的幾個月,很投入地沉浸在學術當中,是我讀了二十年書以來最專注的幾十個星期,為了讀完那些根本不能讀完的reading,很多時候連續一兩天都足不出門,最多只會推開房門,走到那個共用的廚房煮點東西餵飽自己。所以你常常帶着奇怪的語氣,在電話筒裏問我,為什麼每個星期都要從宿舍走一大段路到郵局,再排長長的人龍去買一枚1.33鎊的郵票,而不一次過買十枚八枚方便自己。其實就是為了每個星期一,找個藉口,離開那狹小的房間,呼一口大英帝國的自由空氣。
這幾個月的時間,除了錯過區議會選舉和立法會補選的投票之外,其實還是時刻留意着這個伴我長大的香港所發生的大小事,甚至覺得比以往有更清楚的了解。或許是生活的距離遠了,看的角度闊了;又或者因為有了「時差的優勢」,你知道現在香港發生的大事通常都發生在深夜凌晨,無論是搞革命抑或是政府炒高層,都喜歡選擇午夜場時段。就是因為在倫敦,我可以透過現場直播看看香港又發生什麼事。
不過,當見到香港好像變得愈來愈沒有希望、跟外國朋友聊天他們又總為香港感到擔心和不安的時候,就會因為自己沒有置身其中而感到一種無以名狀的內疚。唯有每次都安慰自己,就算人在香港其實也沒有多大作為。要高呼勇武的話,留在倫敦坐在鍵盤前大叫,也一樣結果,一樣方便。
說是一年的課程,要上的課其實半年就完成,現在只剩考試和論文,時間也鬆動一點,終於可以感受一下這個城市的美好。至少終於有閒情逸致,走進我學校亞非學院旁邊的大英博物館蹓躂一下。另外,我最近也迷上了古典音樂,發現了一個買音樂會門票的網站,以四、五鎊的學生票價就可以入場。倫敦是個欣賞古典音樂的好地方,除了有五大樂團(倫敦交響、愛樂、倫敦愛樂、皇家愛樂、BBC),也有好的書店唱片店去營造一種文藝的氣息。因為有了一種嗜好之後,就會有一股希望不斷知道更多的動力,只有找相關的書來讀才能達至滿足。查令十字街上的書店Foyles,就是我最鍾意的書店。在搬到現址之前,幾個鋪位旁邊的Foyles老店,是董橋形容為「世界最大的書店」。現在新的Foyles就算不是世界最大,至少每個類別的書都很齊全,由宿舍走到唐人街,吃碟好像比香港還要好味的叉燒燒鴨飯,然後到書店打書釘、買書,這樣就是最好的一天。
從書店走回宿舍,總經過那位每晚都在羅素廣場站外擺賣熱狗的大叔,記得去年聖誕你來探我的時候,天氣太冷,我們忍不住買了一隻並且就站在旁邊完成,太多的茄汁還滴污了鞋。九月的時候,你也過來讀書,我們再買熱狗,好嗎?
從台北書展到台灣研究
台北書展(台北國際書展)又來了,愛書人是應該至少去一趟的,跟香港書展是兩回事。不必區分孰優孰劣,只說台北書展特色:大型出版社的攤位,除了堆起書山大賣特賣之外,還擺着幾張枱櫈「傾生意傾版權」;又見到香港和台灣的獨立出版社,聚集一起,組成一年又一年的「讀字」攤位,提供主流以外的閱讀空間。這些景象,不難感覺到台灣人對書的認真。
想起兩年前的台北書展,那時還是本科生,上完課後趕去機場,變身記者飛去台北,約作家、約出版社做訪問,一切恍如昨日。
那個時候,台灣和香港剛經歷完太陽花和雨傘運動,兩地社會開始討論如何總結運動經驗。在書展中,訪問了幾個在台大讀研究院的學生,他們兼職搞獨立出版,出書記下他們眼中的社會運動。像幾個學生所寫的《魯蛇之春》、楊翠老師(學者、同時為學生領袖魏揚的母親)所寫的《壓不扁的玫瑰》。將經驗轉化為動人文字,不只浪漫,而且是最直接最實際的行動去將經驗總結,並且將社會運動的力量保存下來。
去年《號外》其中一期的專題是「台灣作為方法——香港文藝自決的想像」,這個年頭,兩個地方必須互相緊靠互相學習,才能生存。像這幾位研究生,他們重視經驗、重視文字的態度,就是我們應該向台灣學習的其中一種方法。這次訪問的經驗,是我活生生感覺到台灣作為方法的可能。我現在研究台灣政治,也是相信台灣的政治經驗,可以成為香港的方法。
很多人都問,為什麼在英國讀台灣政治?這要從我學校說起。以前曾經寫過我所就讀的亞非學院,一百年前成立,本身為了訓練一班殖民官員到亞洲非洲進行管治。一百年後,英國不再「日不落」,但學校仍然屹立,繼續專門研究亞洲非洲地區政治。所以學校其中一個特色,就是有十個大大小小的地方研究中心,當中最活躍、舉辦最多學術活動的,一定要數台灣研究中心,單在上個學年就舉行了差不多五十場活動。
或者很難想像在英國的學校怎樣講台灣、讀台灣?只要看看這些活動的講者、內容,你就會知道亞非學院的台灣研究,絕對不是請客食飯。兩年前,林生祥來過表演、馬世芳上年暑假時來過做講座、下個星期劉克襄來,談台灣當代文學,還未計學術界中做台灣研究的頂尖學者。這樣的「卡士」、陣容,就算在台灣也不易見到,反而遠在倫敦的亞非學院,差不多每個星期都可以遇到。
兩年前去台灣採訪,沒有想過現在竟然投入台灣研究。回想當日在台北落機,已經深夜了,翌日書展就開幕,所以從機場乘的士直駛酒店,公路上幾乎沒有其他車輛,車窗外的冷風滲入,打在面上。那是我首次離開香港工作,興奮同時,望出窗外覺得世界好像有點不一樣。昨夜步出亞非學院的圖書館,一陣冷風吹個正着,忽然間,世界好像重疊了。
內文 : 孤島
讀書研究的生活必須規律,無論在倫敦抑或台北都一樣,都是起床、吃飯、工作、然後回家;聖誕也好佛誕也好,都跟我們沒有關係,因為研究生的日曆每一天都是黑色的:沒有假期、沒有休息。
做研究的生活規律之餘,而且孤獨,當台灣的麥當勞最近也可以自助點餐的時候,真的可以一天到晚完全不用開口說一句話。所以no man is an island這句說話其實不對,每個研究生其實都是一座寂寞的孤島。
難怪久不久就有報導說,要多多關注研究生的心理健康,最近美國有研究發現:研究生比一般人感到抑鬱焦慮的機會超出六倍。人的情緒就像一個循環,總會有固定時間的潮起潮落。我的專欄一直以來都寫讀書的生活,讀者或多或少應該捕捉得到我最近的情緒狀態處於什麼位置。
我在台北住古亭、工作的地方在大安,之前氣溫還在三十度以下,可以穿過大安森林公園慢慢走到辦公室,總見到一群大媽聚集晨運、幾隻松鼠跑來跑去,還有一對又一對的男女男男或女女在拍拖在親熱。但六月未到,台北已經熱得像火爐,看新聞說今年台灣香港都一樣,都是破紀錄的炎夏。一到室外已經全身濕透、幾乎立即溶掉,我差點以為自己是瑪利歐,去了會噴火有熔岩的世界。
因為只在台北待半年左右,可以租住選擇的地方都沒有太多,最後選了一間小小的劏房,就在一棟老舊的大廈裏面。房間樓底很高,台灣人說這些是「樓中樓」,床就在閣樓上面。對於常常在家工作的人來說,書枱跟床的距離還是愈遠愈好,分成兩層就最好不過。不過劏房沒有窗口,外面天晴抑或下雨都不知道;而且沒有廚房,一天三餐都要在外面解決,思考「晚餐吃什麼」就成為每日最大的難題。
讀書人容易覺得孤獨和失落,不過反過來也一樣容易快樂和滿足,到書店逛逛然後捧著一堆新書回家就是最好的方法。最近讀江勇振教授寫的《舍我其誰:胡適》(剛剛出到第四部)讀得入神,讀胡適先生如何走上留學的路、又如何從修讀農學轉到哲學。胡適是留學生,我也是留學生,就算永遠不可能成為胡適,也要以胡適先生作為目標,奮鬥一下。
最近還有一件小事為我的苦悶生活帶來一點歡樂。在台灣銷費,無論飲食玩樂都總有張發票(即單據),台灣人總會收集這些發票,為的是參加由政府舉辦、每兩個月一次的發票號碼大抽獎,特別大獎的獎金是1000萬新台幣。
去過我住處的朋友都笑我像獨居老人,因為我有個裝滿發票的信封。而且每晚回家之後,總會將當日的發票資料輸入手機的「雲端發票app」,方便「對獎」。最近終於開獎,在我一共百多張發票之中,有兩張中了「六獎」,共得400元正,真是可喜可賀,對嗎?
大留學潮
眨眼來了倫敦差不多三個月,開學之後一直大忙,讀了很多課程相關的書和文章,充實到不得了。因為忘我投入學海,很快就適應新生活。這裏的生活簡單,就是讀書和照顧以往不需自己照顧的三餐飲食,即買餸煮飯。機械一般的生活,日復一日,時間轉眼就過。
身邊大半的同學都來自不同國家,大家最常講的都是記掛自己老家,念茲在茲的都是家人和朋友、還有天氣和食物。我還記掛以前常常流連書店的日子,來回掃射「豬肉枱」上的變化,哪本書是新出版哪本書搬上架了,基本上都掌握一二。現在要在倫敦讀新出版的中文書,動輒要女友寄包裹飛越半個地球才能讀到,運費跟書價看齊(甚至更貴),實在太過奢侈,所以至今只寄過一本、讀過一本。寧願寫下書單,待回港之時才買過痛快。而那本越洋寄來的書,是和自己非常貼切的一本書——《大留學潮》。
貼切因為自己是個留學生,而今時今日也是千百年一遇的「留學大潮」。二月(2015年)的一期《經濟學人》,指在2013年尾,世界各地的中國留學生數目接近110萬,是史上最多。單計在美國就讀學士學位的中國留學生就超過11 萬人,非常嚇人。《大留學潮》的作者張倩儀(前商務印書館總編輯),寫的不是今時今日的留學大潮,而是寫那動盪到不得了的二十世紀初。單論人數,那時的留學生數目比現在少千百倍,但對中國的影響卻隨時大千萬倍。
現在的留學生,是為了求學求知識,說穿了是求一張「沙紙」;當年留學生想的卻是救國救民,希望學習別國之長、補中國之短。1905年科舉制的結束,標誌着海外留學潮的開始,書的其中一節「新科舉洋進士」,點出了留學生的精英地位,相當於科舉制下最高級的進士。清末民初的中國精英,第一等是出國的留學生(特別是得到公費資助留學的學生);而次一等的精英,就要數在國內大學讀書的學生。
兩種精英的其中一大分別,是學生的心態,而這又可見於內地大學的特色。中國第一代翻譯家嚴復的孫女、現在於加州帕克萊大學任教的學者葉文心,研究民國時期的大學。她所寫的《民國時期大學校園文化》就講了民初時期,不同院校的獨有文化。像聖約翰大學,是典型的精英西化學校,一般學生都不熱衷政治,讀課程主要關於英文訓練和科學學科。即使對社會事務較關心的復旦大學,後來亦因為經費問題,提供更多與職業訓練相關的課程,吸引更多學生報讀、增加學費收入。復旦將重心由社會學科主導改變為職業導向,犧牲的就是相對關心政治的傳統。
至於出國留學的精英,可以說是任重道遠。一方面學習現代化的知識,希望拯救陷於水深火熱的中國,從登上輪船開始已經滿腦子科學救國、實業救國等理想,他們就是打開長年封閉積弱的中國的一道鑰匙。無論這些留學生是否意會到這份責任,他們的一舉一動都影響外國人對中國的印象。
當時留學的難度,相比現在都困難得多,無論是飄洋的旅程抑或經濟狀况,跟今天的「留學」都不能同日而語。
今天坐十多個小時長途機已經覺得痛苦不堪,那時候要到歐洲,就要坐船經印度到非洲才能進入歐洲,頭暈嘔吐是肯定的。至於在外地生活,像打理家務、煮飯煲水,在當時中國男女性別定型之下的年代,處理這些家務不單單是「由零學起」,更要衝破心理障礙、突破男女之間的想像。就算是全國最精英的救國青年,都要做家務。
民國初年,中國國力疲弱得很,要出國留學談何容易。書中提到當年家境不俗的巴金,想要留學法國也幾乎要傾家蕩產,所以巴金的哥哥曾經勸他暫緩計劃,待家庭先儲點錢。但作為幼子的巴金堅持到法國,他哥哥也只能放棄前途、全力資助老弟留學。巴金去到法國之後,哥哥寫信問他外面世界究竟是如何,希望巴金分享一下。大哥為了成全老弟的理想而犧牲自己,這是兄弟之情,也是余華小說《兄弟》中的:「即使生離死別,我們還是兄弟」。
留學不容易,更遑論救國。不過如果我們不是將救國理解為那種「超級英雄式」的拯救世界,單單是出國留學、開開眼界,已經是踏出救國的第一步。像當年的其中一個留學熱點——法國,留學生對法國的最深印象,不是花都的浪漫,而是當地中小學對學生的管理。像寄宿學校中的嚴格作息時間、注重清潔衛生等,這種劃一的規律,對當時留學生來說是難以想像的。但一個國家要富強,良好的國民質素是首要條件。這也解釋了為什麼蔣介石的南京政府,為什麼在1920年代取得政權之後推出《新生活運動綱要》。這份綱要所要求的,就是衣食住行都要有規律,然後再談禮義廉恥。
大學生是浪漫的(前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說),留學生在外地應該更加浪漫。書中提到胡適先生在美國讀書時,他在1916年的時候,分別收到1210封信和寫了1040封信。即使今日科技發達,留學生也未必常常跟老家親人朋友聯絡,遑論書信,但胡適就平均一日寫近三封信。這千多封信中,又有多少是情書呢?
提到留學的浪漫,不得不談徐志摩,因為他跟劍橋的浪漫故事實在是個美麗的誤會。讀劉禾教授的《六個字母的解法》時,就有講到徐志摩的故事。首先,他在英國的時候不是劍橋大學的正式學生,他只是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的特別生,徐志摩在大部分的時間,甚至是住在距離劍橋頗遠的小鎮Saxton,所以徐志摩究竟在劍橋逗留過幾長的時間,都值得疑問。另一個誤會,是徐志摩推崇備至的康河,也一點都不浪漫。因為這條河是劍橋祼體協會的活動熱點。當徐志摩說「甘心做一條水草」的時候,其實同時有很多人在水草間祼泳,或許也是這個原因才令徐志摩如此「甘心」。
上一代國人的留學故事,其實都不是徐志摩的康橋故事。因為當時的時代背景,本身已經很困難。他們代表的中國,不是今天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強國,而是面對列強瓜分的中國;他們就算得到國家的公費資助,其實也只是國家打敗仗的庚子賠款,所以胡適才會說「留學者我國之大恥也」這句重話。這是上個世紀的留學歷史,也是今個世紀中國留學生所不能想像的歷史。
在倫敦的半年
V,帶來倫敦的那疊信紙,轉眼寫剩幾張,提醒我在這個跟香港很相似的城市已經生活了半年有多。離開香港之前,跟你許下承諾,要每個星期跟你寫一封信,除了交功課那幾個忙到發瘋的星期之外,我也守了諾言。對上的幾個月,很投入地沉浸在學術當中,是我讀了二十年書以來最專注的幾十個星期,為了讀完那些根本不能讀完的reading,很多時候連續一兩天都足不出門,最多只會推開房門,走到那個共用的廚房煮點東西餵飽自己。所以你常常帶着奇怪的語氣,在電話筒裏問我,為什麼每個星期都要從宿舍走一大段路到郵局,再排長長的人龍去買一枚1.33鎊的郵票,而不一次過買十枚八枚方便自己。其實就是為了每個星期一,找個藉口,離開那狹小的房間,呼一口大英帝國的自由空氣。
這幾個月的時間,除了錯過區議會選舉和立法會補選的投票之外,其實還是時刻留意着這個伴我長大的香港所發生的大小事,甚至覺得比以往有更清楚的了解。或許是生活的距離遠了,看的角度闊了;又或者因為有了「時差的優勢」,你知道現在香港發生的大事通常都發生在深夜凌晨,無論是搞革命抑或是政府炒高層,都喜歡選擇午夜場時段。就是因為在倫敦,我可以透過現場直播看看香港又發生什麼事。
不過,當見到香港好像變得愈來愈沒有希望、跟外國朋友聊天他們又總為香港感到擔心和不安的時候,就會因為自己沒有置身其中而感到一種無以名狀的內疚。唯有每次都安慰自己,就算人在香港其實也沒有多大作為。要高呼勇武的話,留在倫敦坐在鍵盤前大叫,也一樣結果,一樣方便。
說是一年的課程,要上的課其實半年就完成,現在只剩考試和論文,時間也鬆動一點,終於可以感受一下這個城市的美好。至少終於有閒情逸致,走進我學校亞非學院旁邊的大英博物館蹓躂一下。另外,我最近也迷上了古典音樂,發現了一個買音樂會門票的網站,以四、五鎊的學生票價就可以入場。倫敦是個欣賞古典音樂的好地方,除了有五大樂團(倫敦交響、愛樂、倫敦愛樂、皇家愛樂、BBC),也有好的書店唱片店去營造一種文藝的氣息。因為有了一種嗜好之後,就會有一股希望不斷知道更多的動力,只有找相關的書來讀才能達至滿足。查令十字街上的書店Foyles,就是我最鍾意的書店。在搬到現址之前,幾個鋪位旁邊的Foyles老店,是董橋形容為「世界最大的書店」。現在新的Foyles就算不是世界最大,至少每個類別的書都很齊全,由宿舍走到唐人街,吃碟好像比香港還要好味的叉燒燒鴨飯,然後到書店打書釘、買書,這樣就是最好的一天。
從書店走回宿舍,總經過那位每晚都在羅素廣場站外擺賣熱狗的大叔,記得去年聖誕你來探我的時候,天氣太冷,我們忍不住買了一隻並且就站在旁邊完成,太多的茄汁還滴污了鞋。九月的時候,你也過來讀書,我們再買熱狗,好嗎?
從台北書展到台灣研究
台北書展(台北國際書展)又來了,愛書人是應該至少去一趟的,跟香港書展是兩回事。不必區分孰優孰劣,只說台北書展特色:大型出版社的攤位,除了堆起書山大賣特賣之外,還擺着幾張枱櫈「傾生意傾版權」;又見到香港和台灣的獨立出版社,聚集一起,組成一年又一年的「讀字」攤位,提供主流以外的閱讀空間。這些景象,不難感覺到台灣人對書的認真。
想起兩年前的台北書展,那時還是本科生,上完課後趕去機場,變身記者飛去台北,約作家、約出版社做訪問,一切恍如昨日。
那個時候,台灣和香港剛經歷完太陽花和雨傘運動,兩地社會開始討論如何總結運動經驗。在書展中,訪問了幾個在台大讀研究院的學生,他們兼職搞獨立出版,出書記下他們眼中的社會運動。像幾個學生所寫的《魯蛇之春》、楊翠老師(學者、同時為學生領袖魏揚的母親)所寫的《壓不扁的玫瑰》。將經驗轉化為動人文字,不只浪漫,而且是最直接最實際的行動去將經驗總結,並且將社會運動的力量保存下來。
去年《號外》其中一期的專題是「台灣作為方法——香港文藝自決的想像」,這個年頭,兩個地方必須互相緊靠互相學習,才能生存。像這幾位研究生,他們重視經驗、重視文字的態度,就是我們應該向台灣學習的其中一種方法。這次訪問的經驗,是我活生生感覺到台灣作為方法的可能。我現在研究台灣政治,也是相信台灣的政治經驗,可以成為香港的方法。
很多人都問,為什麼在英國讀台灣政治?這要從我學校說起。以前曾經寫過我所就讀的亞非學院,一百年前成立,本身為了訓練一班殖民官員到亞洲非洲進行管治。一百年後,英國不再「日不落」,但學校仍然屹立,繼續專門研究亞洲非洲地區政治。所以學校其中一個特色,就是有十個大大小小的地方研究中心,當中最活躍、舉辦最多學術活動的,一定要數台灣研究中心,單在上個學年就舉行了差不多五十場活動。
或者很難想像在英國的學校怎樣講台灣、讀台灣?只要看看這些活動的講者、內容,你就會知道亞非學院的台灣研究,絕對不是請客食飯。兩年前,林生祥來過表演、馬世芳上年暑假時來過做講座、下個星期劉克襄來,談台灣當代文學,還未計學術界中做台灣研究的頂尖學者。這樣的「卡士」、陣容,就算在台灣也不易見到,反而遠在倫敦的亞非學院,差不多每個星期都可以遇到。
兩年前去台灣採訪,沒有想過現在竟然投入台灣研究。回想當日在台北落機,已經深夜了,翌日書展就開幕,所以從機場乘的士直駛酒店,公路上幾乎沒有其他車輛,車窗外的冷風滲入,打在面上。那是我首次離開香港工作,興奮同時,望出窗外覺得世界好像有點不一樣。昨夜步出亞非學院的圖書館,一陣冷風吹個正着,忽然間,世界好像重疊了。
最佳賣點 : 為什麼留學?為什麼浪遊?
他所選擇的,其實是一種精神生活方式。
完美融會冷靜與熱情的篇章,記錄了青年亞然求知若渴的「純真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