視覺、性別與權力: 從劉吶鷗、穆時英到張愛玲的小說想像
| 作者 | 梁慕靈 |
|---|---|
| 出版社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 商品描述 | 視覺、性別與權力: 從劉吶鷗、穆時英到張愛玲的小說想像:內容簡介劉吶鷗的視覺化小說為何會從台灣登陸到上海租界?穆時英如何運用小說視覺化表述,表現上海貧富懸殊的半殖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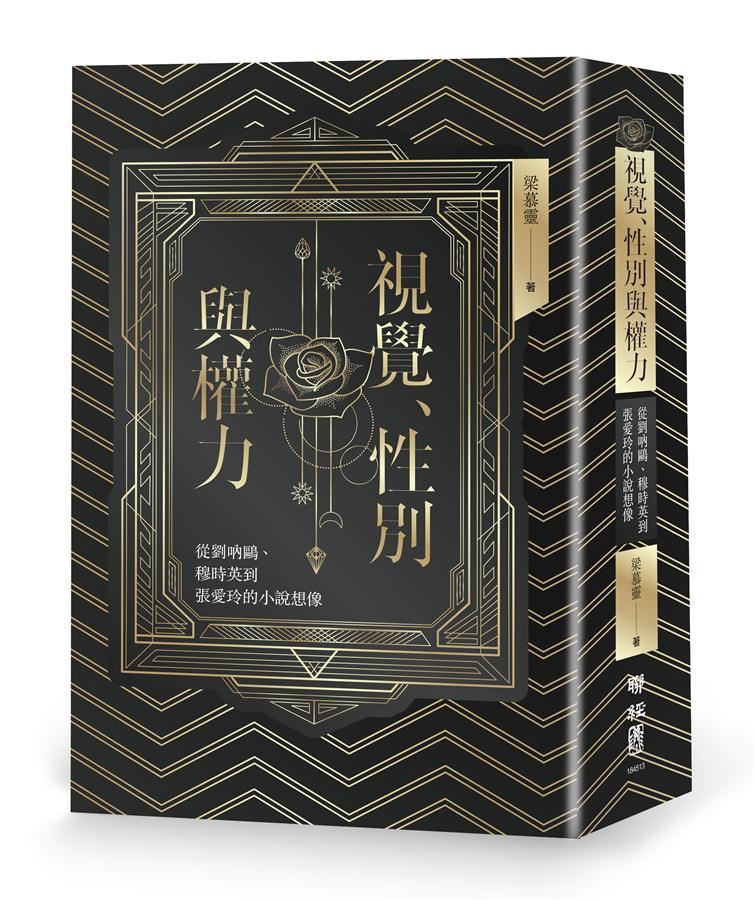
| 作者 | 梁慕靈 |
|---|---|
| 出版社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 商品描述 | 視覺、性別與權力: 從劉吶鷗、穆時英到張愛玲的小說想像:內容簡介劉吶鷗的視覺化小說為何會從台灣登陸到上海租界?穆時英如何運用小說視覺化表述,表現上海貧富懸殊的半殖 |
內容簡介 劉吶鷗的視覺化小說為何會從台灣登陸到上海租界?穆時英如何運用小說視覺化表述,表現上海貧富懸殊的半殖民地處境?張愛玲又如何以這種方法對傳統和現代中國做出觀察與反思?小說作為現代中國人想像、敘述「中國」的開端,由梁啟超提倡「新小說」起,經歷了過百年的變化。不論在形式或內容上,小說的種種改變均與現代中國社會各方面的變化息息相關。王德威在一九九三年提出關注「想像中國」的議題,思考國人怎樣通過小說這種敘事模式去想像中國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在《視覺、性別與權力:從劉吶鷗、穆時英到張愛玲的小說想像》一書中,作者梁慕靈以「視覺性」的角度,審視小說另一種想像中國的方法,目的在於重現當時在殖民地台灣和半殖民地上海中成長的新一代作家,他們「想像中國」的「新」角度,並重點分析劉吶鷗、穆時英和張愛玲的小說,觀察這些小說怎樣以「視覺」的方式來想像中國,這種方式又如何反映和形塑中國的現代經驗。三○年代興起於上海的新感覺派當中,劉吶鷗和穆時英的小說具有強烈的視覺化表述特徵。這種小說表述模式並不是完全由中國本土文化場域所孕育,而是劉吶鷗這位台灣人經過迂迴的路線引入。這種新的小說表述模式帶來了新的想像方法,原因在於它是經由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到本土化的複雜過程而生成。《視覺、性別與權力》探討穆時英和張愛玲怎樣改造和「模擬」「殖民者凝視」,表現出新一代對「現代」中國的想像。梁慕靈認為劉吶鷗、穆時英和張愛玲三位作家的「模擬」策略,由於時代和位置的不同而顯出差異,但是這種「模擬」並不是純粹的複製,而是一種再創造,顯示的是有別於主流的「另一種」想像中國的方法。本書關注上述三位作家在小說、電影、理論和翻譯方面如何展露一種新的想像模式,他們為中國現代文學場域引入並創造了「另一種」的想像中國的方法,顯示了中國現代小說在現實主義的陳述模式和浪漫主義的抒情模式以外,尚有其他方式去構想和建築現代中國。 《視覺、性別與權力》輯一以翻譯和視覺性的角度討論劉吶鷗、穆時英和張愛玲三位作家的小說創作。第二章首先探討曾經歷日治時期的臺灣作家劉吶鷗,其富有殖民地色彩的成長背景,使這位臺灣作家的作品具備多元現代性的特質,包含了歐洲、日本、臺灣和中國大陸的語言和文化特徵。第三章討論中國三○年代興起於上海的新感覺派,當中劉吶鷗和穆時英的小說具有強烈的視覺化表述特徵。第四章討論了劉吶鷗、穆時英和張愛玲的小說怎樣以「電影視覺化表述」去想像他們心目中的中國。第五章則探討中國三、四○年代興起的現代主義思潮,如何為中國現代文學場域引入了具有殖民主義文學特質的小說,當中的視覺意識在不同程度上影響了劉吶鷗、穆時英和張愛玲的小說。 輯二以張愛玲為研究焦點,從性別、視覺、離散及地域的角度討論張愛玲的作品具有怎樣的獨特性。第六章以記憶為題,探討在張愛玲整個小說創作生涯中,具有傳承經驗作用的「講故事」敘述模式的衰亡過程,以及這種模式衰落以後,張愛玲的小說如何轉化成「小說」模式的經過,從而思考當中記憶與歷史的關係。第七章探討張愛玲的電影劇作如何一方面採納通俗劇模式,另一方面卻以不同的「技巧」去逐步改變觀眾/讀者對這一模式的渴求。第八章關注張愛玲作品如何表現她心目中的香港。第九章以離散的角度討論張愛玲後期小說的風格。第十章則以離散及女性自傳體小說的角度,討論張愛玲後期作品的特色和意義。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梁慕靈香港公開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副教授,創意藝術學部主任及田家炳中華文化中心主任。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取得哲學博士、哲學碩士及榮譽文學士資格,亦取得香港大學學位教師證書。曾任恒生管理學院中文系助理教授及副系主任,兼任中國語言及文化研習所副所長。研究興趣為中國現當代文學、文化和電影理論及創意寫作教育,論文見於《清華學報》、《政大中文學報》、《中國現代文學》等學術期刊,並曾出版及編著《博物館的變與不變:香港和其他地區的經驗》及《數碼時代的中國人文學科研究》。同時喜愛文藝創作,曾得到《聯合文學》第16屆小說新人獎短篇小說首獎,作品散見香港和臺灣的文學雜誌和報章。
產品目錄 第一章 想像中國的另一種方法輯一第二章 混種文化翻譯者的凝視--劉吶鷗對殖民主義文學的引入和轉化第三章 由翻譯到「模擬」--劉吶鷗、穆時英和張愛玲小說的「視覺性」第四章 劉吶鷗、穆時英和張愛玲小說「電影視覺化表述」的確立、本土化與改造第五章 性別觀看與殖民觀看--從穆時英到張愛玲小說的「視覺性」變化輯二第六章 從「講故事」到「小說」--張愛玲小說中的記憶轉化第七章 「反媚俗」--張愛玲電影劇作對通俗劇模式的超越第八章 他者‧認同‧記憶--張愛玲的香港書寫第九章 張愛玲的離散意識與後期小說風格第十章 張愛玲後期作品中的女性離散者自我論述第十一章 終章附錄參考書目論文初出一覽致謝後記
| 書名 / | 視覺、性別與權力: 從劉吶鷗、穆時英到張愛玲的小說想像 |
|---|---|
| 作者 / | 梁慕靈 |
| 簡介 / | 視覺、性別與權力: 從劉吶鷗、穆時英到張愛玲的小說想像:內容簡介劉吶鷗的視覺化小說為何會從台灣登陸到上海租界?穆時英如何運用小說視覺化表述,表現上海貧富懸殊的半殖 |
| 出版社 /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 ISBN13 / | 9789570851823 |
| ISBN10 / | 9570851821 |
| EAN / | 9789570851823 |
| 誠品26碼 / | 2681666232004 |
| 頁數 / | 544 |
| 開數 / | 25K |
| 注音版 / | 否 |
| 裝訂 / | H:精裝 |
| 語言 / | 1:中文 繁體 |
| 級別 / | N:無 |
最佳賣點 : 小說作為現代中國人想像、敘述「中國」的開端,
劉吶鷗的視覺化小說為何會從台灣登陸到上海租界?
穆時英如何運用小說視覺化表述,表現上海貧富懸殊的半殖民地處境?
張愛玲又如何以這種方法對傳統和現代中國做出觀察與反思?。
內文 : 內文選摘(節錄)
第六章 從「講故事」到「小說」──張愛玲小說中的記憶轉化
張愛玲的創作高峰期正值中國歷史的一段夾縫之中,由十九世紀末起不斷發展的啟蒙與革命的大敘述路線,在這段期間進占主流地位。代表著中國傳統社會的社群記憶,被來勢洶洶的歷史進程猛烈衝擊,中國傳統的「記憶的氛圍」不斷被稀釋,現代人日益與傳統社群脫離,傳統文化的延續性受到摧毀,這種情況於文學的表現上尤為明顯。與這種文學主流不同,張愛玲十分重視傳統記憶的承傳,並對這種記憶的失落深有體會:
個人即使等得及,時代是倉促的,已經在破壞中,還有更大的破壞要來。有一天我們的文明,不論是昇華還是浮華,都要成為過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涼」,那是因為思想背景裏有這惘惘的威脅。
這段文字中提及的「文明」,指千百年來人類經驗的累積,以往的生活智慧與感情成為現代人的記憶,讓人以此繼續生活下去。張愛玲所言的「破壞」,可以理解為這種經驗的迅速貶值──過往的人以血汗累積的生活經驗,本來是一代傳一代、極富價值的遺產,現在卻因時代迅速改變而變得毫無價值──這就造成現代人生活中記憶的氛圍越趨淡薄,亦出現與傳統以至世界分裂的意識。張愛玲當時身處於戰亂的時代,而經驗在戰爭中更是一無是處──在戰爭的破壞下,任何「文明」都有可能被摧毀至滅絕,故此張愛玲對人類將要失去「文明」感到有「惘惘的威脅」。面對這種情況,張愛玲選擇在小說中保留傳統敘述的方式──「講故事」,讓傳統記憶可以在這種敘述方式得到保留之後,得以繼續存在。
綜觀張愛玲整個的創作生涯,她對傳統及現代性的看法並不是固定的,而是隨著她的個人經歷、創作生命的成長以及思考而不斷轉變,這就造成她前後期的文學創作風格迥然不同。本章希望借用本雅明有關傳統與記憶的思考,特別是他對於「講故事」與「小說」兩種敘述形式與現代性關係的評論,來梳理張愛玲小說創作風格演變的情況,並探討這種情況對我們的意義。本章認為,在張愛玲早期的小說中,她較為側重於傳統記憶的表述,其思想上的荒涼感正是出於現代性歷史對傳統記憶的破壞而來。這些經過多年積聚的文化記憶,仿如無形的纖維,用以維繫中國人之間的集體記憶,以及界定民族自我身分。然而這種記憶隨著現代性歷史進程而有湮沒的危機,故此張愛玲才自言有「荒涼」的思想背景。
越至後期,張愛玲小說中的記憶就越趨淡薄,表現出現代人在意識上與傳統的斷層。本章以記憶為題,探討在張愛玲整個的小說創作生涯中,具有傳承經驗作用的「講故事」敘述模式的衰亡過程,以及這種模式衰落以後張愛玲的小說如何轉化成「小說」模式的經過,從而思考當中記憶與歷史的關係。本章的研究脈絡建基於張愛玲小說的不同階段分期,根據創作時間、地域做出分期,同時經本章關於小說內部風格轉變的研究以後,反過來亦能佐證相關的分期研究;亦希望在時間及空間這兩個要素以外,發掘另一個劃分張愛玲各個小說創作時期的判斷點,以突顯張愛玲不同時期的小說風格特色。
本章首先以張愛玲的早期小說為重心,梳理出由〈第一爐香〉到〈紅玫瑰與白玫瑰〉中記憶的突然轉化,以及「講故事的人」由主導故事的位置逐漸退隱的情況,印證著本雅明所言「講故事」傳統的消散標誌著現代人「經驗」衰亡的狀況。本章接著討論張愛玲的中期小說,分析由〈十八春〉到《赤地之戀》「記憶」的轉變情況,特別是〈十八春〉與〈小艾〉作為無產階級文學實驗,與《秧歌》「平淡而近自然」的美學特色的關係。最後本章將引用本雅明有關普魯斯特的「非意願記憶」與「意願記憶」的論述,觀察張愛玲後期小說中表現的「震驚」,以此突顯出張愛玲這一階段的小說創作在風格上的強烈轉變與記憶的密切關係。
「講故事的人」的出場與消隱──張愛玲早期小說的記憶轉化
張愛玲在踏入文壇時即以「講故事的人」的姿態出現,這一點最能體現她與中國傳統小說之間的傳承關係。在她早期的散文〈到底是上海人〉中,已表明了作為一個「講故事的人」的自覺:「我為上海人寫了一本香港傳奇……寫它的時候,無時無刻不想到上海人,因為我是試著用上海人的觀點來察看香港的。只有上海人能夠懂得我的文不達意的地方。」在張愛玲早期發表的一系列小說中,她自己作為「講故事的人」的聲音較為明顯,她自覺地擔當有如中國傳統說書人般的身分,在小說中常常可找到她的看法及感慨,這與中國傳統說書人常常把自身凌駕於故事之上的敘述方式非常相似。本雅明認為,「故事」這種傳統的敘事模式有其特別之處,就是它在敘事中會蘊含某些「實用」的東西,講故事者是一個對讀者有所指教的人,因為故事包含著講者所分享的經驗與教訓。但是「小說」這種現代敘事模式卻對人缺乏指教,讀者無法得到作者的「教誨」。因此要判別張愛玲早期小說是否具有講故事式的傳統敘事特質,除了要找出「講故事的人」這個敘述者有否出場以外,亦可憑著文本中「講故事的人」的聲音是否明顯去決定。
本章借用本雅明對「講故事的人」的兩種分類方法─一種是來自遠方的來客,另一種是蟄居某地、對本土本鄉的掌故與傳統非常熟稔的原住民──分析張愛玲早期小說中「講故事的人」的獨特位置。在這些小說中,張愛玲重疊了兩種「講故事的人」的形象:既是從香港回來,向聽眾「上海人」述說香港傳奇;另一方面又熟悉上海本土傳統掌故,於是擔當著一個向土著傳授本土經驗的角色。這個「講故事」的位置直接決定了張愛玲早期小說創作的成就。下文將根據本雅明相關的討論,把張愛玲早期的小說創作歸納為遠方傳奇與本土經驗兩大類型,並整理出各篇小說中的講故事特質。
在第一種遠方傳奇類型中,張愛玲以香港作為遠方傳奇的舞臺,講故事的對象是上海人。她於一九四三年首次發表的小說〈沉香屑─第一爐香〉及〈沉香屑──第二爐香〉,就是以上海人為講故事的對象,為他們介紹香港傳奇。在這一類型的作品中,多以空間上的遠距離故事作為題材,以加強故事中「傳奇」的意味。除此以外,這一類型的小說也會以時間上的距離增添作品的「傳奇」意味,例如〈金鎖記〉就是發生在年代久遠的上海的傳奇故事。為了配合這種遠距離故事的傳奇色彩,張愛玲多用上中國古典小說中常見的說書口吻及用語,以講故事的形式去書寫作品。屬於這一類作品的包括〈第一爐香〉、〈第二爐香〉、〈茉莉香片〉、〈傾城之戀〉、〈金鎖記〉以及〈連環套〉,以下將從三方面分析這一類作品中不同的「講故事」元素。
首先,「講故事的人」在這些作品中位置明顯,常常會流露作者的個人觀感及評論。例如在〈第一爐香〉開首即明言「我」作為一個講故事的人的身分:「聽我說一支戰前香港的故事……」然後「講故事者」開始述說故事:「在故事的開端,葛薇龍,一個極普通的上海女孩子,站在半山裡一座大住宅的走廊上……」「講故事者」先提出「葛薇龍是一個極普通的上海女孩子」的觀點,然後才述說她以後「不普通」的經歷。
在〈第二爐香〉中,張愛玲以三段的篇幅交代講故事者「我」得知這個故事的途徑:「克荔門婷興奮地告訴我這一段故事的時候……」當中又加插「講故事者」個人的感慨:「說到穢褻的故事,克荔門婷似乎正有一個要告訴我,但是我知道結果那一定不是穢褻的,而是一個悲哀的故事。人生往往是如此──不徹底……一個髒的故事,可是人總是髒的;沾著人就沾著髒。」故事的性質不是「穢褻」而是「悲哀」的,這不是故事中的人物的看法,與接下來的感慨相同,都是來自「講故事者」的看法。
在〈茉莉香片〉中明顯可見「講故事的人」的存在:「我將要說給您聽的一段香港傳奇,恐怕也是一樣的苦──香港是一個華美的但是悲哀的城。」這裡張愛玲不但明言自己「講故事的人」的身分,更加插了自己個人的觀感:香港是一個華美的但是悲哀的城。〈傾城之戀〉的開首亦仿如說書人的獨白:「胡琴咿咿啞啞拉著,在萬盞燈的夜晚,拉過來又拉過去,說不盡的蒼涼的故事──不問也罷!」這一句並不是故事的情節,而是用以營造說故事的氣氛,再配合胡琴,故事才得以開展,當中的「不問也罷!」更是一個講故事者的感嘆。在故事的結尾,「講故事者」又抒發了她個人的感慨:「傳奇裏的傾國傾城的人大抵如此」,顛覆了傳統對傾國傾城的女子的觀念。
同樣,〈金鎖記〉中首段亦著力以描寫月光來營造說故事的氣氛:
三十年前的上海,一個有月亮的晚上……我們也許沒趕上看見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輕的人想著三十年前的月亮該是銅錢大的一個紅黃的濕暈,像朵雲軒信箋上落了一滴淚珠,陳舊而迷糊。老年人回憶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歡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圓、白;然而隔著三十年的辛苦路望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帶點淒涼。
這一段中明顯貫徹著講故事者的口吻,可以想像「講故事者」帶領著不同年紀的聽眾回望月色,特別是末二句的結論並不屬於故事人物,而是屬於這位「講故事者」,更能顯出「講故事者」凌駕於故事之上的地位。另外,這段文字中的「我們」表達出「講故事的人」與聽眾之間的關係──「我們」都共同觀看著這場「戲」──一種平等、共同分享經驗的關係。故事的結尾首尾呼應,這種講故事的技巧上承中國傳統小說封閉而圓滿的故事結構,作用是在帶領聽眾經歷一段悲歡離合之後為他們提供安慰,帶有濃厚的說書特色。
至於〈連環套〉更是一個講述廣東養女如何靠婚姻掙扎上游的「歷險故事」。小說開始先交代作者從哪裡得知這個故事─於戲院遇見女主角賽姆生太太。之後作者運用「講故事的人」的口吻開展故事:「賽姆生太太小名霓喜。她不大喜歡提起她幼年的遭際,因此我們只能從她常說的故事裏尋得一點線索。」這裡顯示〈連環套〉這個故事的調侃語調是來自於「講故事者」,顯然與女主角賽姆生太太本人的自述有相當的距離。在〈連環套〉中作者常常向聽眾表露自己的看法:
先後曾經領了好幾個姑娘去,那印度人都瞧不中,她是第七個,一見她便把她留下了,這是她生平的一件得意的事。她還有一些傳奇性的穿插,說她和她第一個丈夫早就見過面。……這一層多半是她杜撰的。
這種向聽眾交代個人看法的模式,是本雅明認為「講故事」這種傳統敘事模式有價值的地方。這不僅是因為故事可以把經驗傳遞給下一代,使這個故事可以繼續傳承下去,亦由於在敘述與接收的過程中,人得以與過去的世界連繫,令人的意識能植根於傳統,成為「記憶」。本雅明認為,「講故事」的價值在於經「講故事者」在敘述中令故事得到添加於重組,以配合新的環境,這正是故事與「小說」的一項重要區別。在上述的例子中,原始文本經過張愛玲這位「講故事者」的更新,添加了個人見解及經驗,令文本具備了本雅明所說的更新的價值,這亦是張愛玲早期作品的價值之一。
第二方面,張愛玲的早期小說常常會著力營造「聽故事」的氣氛。本雅明認為只有在閒散的狀態中,聽者才能不知不覺地進入忘我狀態,這樣故事才能深深地在聽者的記憶中占據位置:
使一個故事能深刻嵌入記憶的,莫過於拒斥心理分析的簡潔凝煉。講故事者越是自然地放棄心理層面的幽冥,故事就越能佔據聽者的記憶、越能充分與聽者的經驗溶為一體,聽者也越是願意日後某時向別人重述這故事。這個溶合過程在深層發生,要求有鬆散無慮的狀況……
在這種閒散的狀態中,傳統經驗得以在不知不覺間深入聽者的記憶。故此「講故事的人」多在故事開始以前,以不同的方法去營造氣氛,或長篇鋪述得知故事的途徑,以達到舒緩的效果。在張愛玲早期作品中可找到很多運用這種手法的地方,例如在〈第一爐香〉中的開首:
請你尋出家傳的霉綠斑斕的銅香爐,點上一爐沉香屑,聽我說一支戰前香港的故事,您這一爐沉香屑點完了,我的故事也該完了。在故事的開端……
這裡模仿傳統說書的環境,讓本來身在不同空間的讀者憑著想像,猶如置身其中般聽著一個故事緩緩開始。而在故事結束時,作者以「這一段香港故事,就在這裏結束……薇龍的一爐香,也就快燒完了」收結,這種首尾呼應、結構完整而封閉的講故事方法,明顯秉承著中國說書的傳統,是中國讀者一貫閱讀小說的習慣,帶有濃烈的文化記憶。
其他作品如〈第二爐香〉:「請你點上你的香,少少的撮上一點沉香屑;因為克荔門婷的故事是比較短的。」;〈茉莉香片〉中:「我給您沏的這一壺茉莉香片,也許是太苦了一點……您先倒上一杯茶─當心燙!您尖著嘴輕輕吹著它。在茶烟繚繞中,您可以看見香港的公共汽車……」;〈連環套〉開首以多達十五段的篇幅交代故事的來源以增加可信性等,都可見張愛玲早期的作品非常著重在故事開始以前先營造講故事的氣氛。本雅明認為,故事不是外在經歷的客觀敘述,而是由個人至集體的活生生的經驗。故事在集體生活之中具有一種凝聚力,融合於講故事者與聽故事者之間的生活經歷之中。故此張愛玲早期的小說,營造出一種與古代說書環境相近的氛圍,使讀者好像回到以往說書的環境一般,較之於她後期的作品,這方面的記憶元素顯得非常明顯。
除了上述有關遠方傳奇的作品以外,張愛玲的早期小說亦有一些取材於上海本土的小說,本章把這些小說劃分為本土經驗小說。這些小說不論在空間或時間上都較接近當時的上海讀者,因此對比上述的遠方傳奇作品,當中的說書用語較少,而講故事者的身分亦較為隱藏。越到後期,「講故事」的元素就更為減少。
與上述類型的作品同樣寫於一九四三年,但由於〈心經〉、〈封鎖〉及〈琉璃瓦〉的故事都發生於當時的上海,遠距離的傳奇意味較為薄弱,因此,在這些作品中較難找到同期作品中「講故事」的元素。其他的作品間歇可見「講故事」元素的出現,但是密度比上述類型大為減少,例如〈花凋〉中對於川嫦的墓碑上所寫的美化了的人生,「講故事者」對此不以為然:「全然不是這回事。的確,她是美麗的,她喜歡靜,她是生肺病死的,她的死是大家同聲惋惜的,可是……全然不是那回事。」除此以外,在文中仍能看見殘留著的「講故事的人」的見解及觀點,例如批評鄭先生是「連演四十年的一齣鬧劇」,而他的夫人則是「一齣冗長單調的悲劇」。在〈鴻鸞禧〉中,作者雖然沒有明顯地站出來發表意見,但她的見解及觀點仍然若隱若現於故事之中。例如對新娘的兩個表妹的描述就帶有一種諷刺的評價。〈殷寶灩送花樓會〉則明寫得到這個故事的來源:女主角殷寶灩上門探望作者,向她哭訴的經過。張愛玲對這個故事的處理極少,彷彿向朋友複述一般,甚至複述她與殷寶灩談論事情的經過,最後又有自己的評價:「我也覺得這是無可挽回的悲劇了。」而在四十年後(一九八三年)張愛玲又為這篇小說補寫了尾聲,當中「講故事者」的態度立場仍然沒變,甚至加插分析殷寶灩與羅潛之愛情悲劇的原因,仿似向聽眾品評小說人物。加添了作者對故事的個人評價,令人感到張愛玲最想表達的就是對〈殷寶灩送花樓會〉中的愛情病症的看法,小說本身反而變得次要,變成了人們之間的談資。甚至在最後,作者自己個人的情緒反客為主:「在這思想感覺的窮冬裡,百無聊賴中才被迫正視〈殷寶灩送花樓會〉的後果。『是我錯』,像那齣流行的申曲劇名。」整篇小說成為了作者自我反思的鋪墊,〈殷寶灩送花樓會〉變成明顯的「張看」之下的故事。
分析張愛玲整個早期小說創作的脈絡,可發現作為記憶的「講故事」元素逐漸減少,與歷史發展的影響有密切關係。當中關鍵的因素大約可以從〈紅玫瑰與白玫瑰〉這篇小說發表後算起。〈紅玫瑰與白玫瑰〉在《雜誌》月刊中連載時,小說開首以「我」作為「講故事者」,後來在一九四六年出版的《傳奇》增訂本中,這個「講故事者」被刪去了,小說中並有不少的改動。最明顯的是小說的開首,《雜誌》月刊中的原文本為:
振保叔叔沉著地說道:「我一生愛過兩個女人,一個是我的紅玫瑰,一個是我的白玫瑰。」聽到這話的時候,我忍不住要笑,因為振保叔叔絕對不是一個浪漫色彩的人。我那時候還小,以為他年紀很大很大……
然後是「講故事者」交代自己聽到這個故事的經過:
他先向屋子裏望了一眼,我弟弟已經睡去了,我坐在燈底下看小說。我嬸娘便道:「不要緊的,這孩子只要捧著一本書,什麼都聽不見。」於是他繼續說下去……振保叔叔的話,前半截我只聽見了一部份。漸漸更深夜靜,那小洋台輕輕往上浮了起來,離衖堂遠了,離星月近了。振保叔叔的話我句句聽明白了,便是他所沒有說的,我也彷彿是聽見了。
而《傳奇》增訂本的版本則是:
振保的生命裏有兩個女人,他說的一個是他的白玫瑰,一個是他的紅玫瑰。一個是聖潔的妻,一個是熱烈的情婦─普通人向來是這樣把節烈兩個字分開來講的。
這裡可見張愛玲後來的創作趨向把「講故事者」隱藏起來,不單把故事的來源刪去,同時亦逐漸把「講故事者」的看法減少。
萬燕把張愛玲後來放棄這種講故事式的寫法視為她成長的標記:
〈紅玫瑰與白玫瑰〉在張愛玲小說創作史上的意義,確實是非比尋常的。這才是屬於她自創的小說形式,從這以後,我們也就再沒有看到她用講故事的方式來寫小說的開場白,如〈桂花蒸 阿小悲秋〉、《十八春》等都是現代小說的面目。成績都應歸功於她這一段的「廢套期」,然而和她小說形式現代化相反的是,讀者相比之下更愛看的是她「廢套期」前的小說,這也真是個二律背反現象。
萬燕的觀察十分細緻,看到〈紅玫瑰與白玫瑰〉是張愛玲小說創作風格轉變的轉捩點,並且顯示這是張愛玲的小說由傳統敘事過渡到現代小說模式的關鍵時間。但本章不同意萬燕視張愛玲選擇放棄傳統敘事為進步的觀點,而希望從歷史的角度做觀察─這個「廢套期」未必由文學內在發展規律而來,更多是一種傳統記憶面對歷史進程的無奈撤出。〈紅玫瑰與白玫瑰〉發表以後,一連串的評論相應適時發表,既對〈紅玫瑰與白玫瑰〉以前的小說做出評價,也對當時張愛玲的寫作做一階段性評議。由〈紅玫瑰與白玫瑰〉於一九四四年五月至七月於《雜誌》月刊中連載算起,直至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才又有〈殷寶灩送花樓會〉一篇小說發表,當中出現了約五個月的真空期,與〈紅玫瑰與白玫瑰〉發表之前張愛玲每月都有新作發表,甚至一個月內發表多於一篇小說及散文的情況不同。這段期間前後出現了多篇評論文章,例如載於三月的胡蘭成〈皂隸.清客與來者〉、四月的傅雷〈論張愛玲的小說〉、五月及六月的胡蘭成〈評張愛玲〉、九月顧樂水的〈《傳奇》的印象〉、十月柳雨生的〈說張愛玲〉、十二月譚正璧的〈論蘇青及張愛玲〉等。這些寫於圍繞〈紅玫瑰與白玫瑰〉前後的評論,不少都集中批評張愛玲偏於絢麗的文字技巧,以及小說中「平凡的意識」。例如顧樂水讚賞過張愛玲的文字為讀者帶來感官的享受後,曲折地贊成迅雨的批評;譚正璧亦認為張愛玲的小說雖然是新舊文學的糅合、新舊意境的交錯,但「無限量的運用便要成為濫調與俗套,本是賴以成功的因素,往往就會是招致失敗的絆腳石。」就連胡蘭成寫於三月的評論也曾批評《封鎖》過分精緻:
我喜愛這作品的精緻如同一串珠鏈,但也為它的太精緻而顧慮,以為,倘若寫更巨幅的作品,像時代的紀念碑式的工程那樣,或者還需要加上笨重的鋼骨與粗糙的水泥的。
至於傅雷那篇著名的〈論張愛玲的小說〉更重點批評〈連環套〉的措詞用語:
處處顯出「信筆所之」的神氣,甚至往腐化的路上走……但到了〈連環套〉,這小疵竟越來越多,像流行病的細菌一樣了:「兩個嘲戲做一堆」……這樣的濫調,舊小說的渣滓,連現在的鴛鴦蝴蝶派和黑幕小說家也覺得惡俗而不用了,而居然在這裏出現。
張愛玲於一九四四年五月即發表〈自己的文章〉回應胡蘭成及傅雷的文章。她在文章中解釋維護自己的創作理念,聲稱自己並不寫「時代的紀念碑式」的文章,但對於有關措詞用語的批評卻是接納的:
至於〈連環套〉裏有許多地方襲用舊小說的詞句──五十年前廣東人與外國人,語氣像《金瓶梅》中的人物……我當初的用意是這樣:寫上海人心目中的浪漫氣氛的香港,已經隔有相當的距離;五十年前的香港,更多了一種時間上的距離,因此特地採用一種過了時的辭彙來代表這雙重距離。有時候未免刻意做作,所以有些過份了。我想將來是可以改掉一點的。
面對各方批評,張愛玲自此刻意改變文字運用的風格,連隨減淡了作品中「講故事者」的形象,使「講故事者」的觀點變得更為內歛,亦取消了舊小說中的「講故事」口吻。
這種「講故事」模式的衰落,本雅明認為是現代性歷史的步伐在文學這個範疇留下痕跡的一個例子。他認為「講故事」本身是一門「重述」的工藝,故事的價值由「講故事者」而來,因為「講故事者」不會只著眼於敘述事情的精華,而是把世態人情沉浸出來,「講故事者」把自身或道聽途說的經歷化為自身的經驗,然後再轉化為聽者的經驗,因此故事中必定包含著「講故事者」的感慨、評論與教訓,「講故事者」是一個對讀者有所教導的人。但歷史進程破壞了這種傳統敘事的生存環境,現代人的感知與意識與傳統發生崩裂,出現了一種新興的現代敘事模式:「小說」。「小說」誕生於離群索居的個人,特別是短篇小說的出現,把口頭敘述從傳統中剝離出來,不再容許說故事的人一代一代地把自身的經驗疊加於故事之中。因此,經驗變得無可交流,「小說」已不能再對人有教誨作用,而且也限制了傳統或舊的事物於新時代的轉化。張愛玲的最早期小說創作,雖然在形式上並不是口述的「講故事」敘述模式,但當中仍然保留了不少「講故事」的元素,可算是對傳統的一種回歸。後來不論張愛玲是自發還是受到外來文學環境的影響,她的創作確是由「講故事」演變為「小說」的模式。這種「講故事」衰亡的趨勢到張愛玲創作的後期更見明顯。她晚年的作品普遍被認為是艱澀難讀,有論者認為這是由於她去國後遠離創作的根源,亦有人認為她的創作才華已經用盡,其實均可以「講故事」的集體記憶衰亡去做出解釋。以後來出版的張愛玲小說〈鬱金香〉為例,就見證著「講故事」元素的褪色是她「枯萎」的一個重要因素。李歐梵在閱讀過這篇張愛玲離開上海前最後的小說〈鬱金香〉以後,有以下的評論:
可惜的是,張愛玲的佚文中「舊」的故事愈來愈多,而新的視角和視野卻愈來愈少。在〈鬱金香〉中幾乎感覺不到敘事者的涵養和看法,敘事語言中多的是交代人物關係,卻少了一份反諷……張愛玲寫舊社會,自從〈金鎖記〉之後,再也表現不出那麼撼人的「張力」。
同樣是寫舊社會的故事,〈鬱金香〉的題材與〈金鎖記〉的同屬一個類型,「張力」效果卻有天淵之別。李歐梵認為這是由於「感覺不到敘事者的涵養和看法」,正正佐證上文對張愛玲的早期寫作生命從一開始的「高峰」轉入以後「低潮」的分析。「講故事」的衰亡不但導致現代人無法交流經驗,亦直接連繫著這一時期張愛玲小說創作的完結。她的創作將逐漸遠離早期的傳統「講故事」模式,經歷與歷史進程更多的對話,與現代敘事模式──「小說」──越走越近。